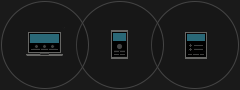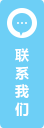|
南方之六 . 竹兰兰
作者: 35公里
|
发布: 2007/10/23 (7:35)
|
阅读: 39166
|
评论: 0
|
静态地址
|
内容源码
南园最常见的花是紫色或者嫩蓝色的牵牛,我们叫做打碗花,据说孩子惹了这种花,会失手打碎家里的瓷器,人们讲,美丽的事物,背后藏着阴险,牵牛花也许就是个例子。但我非常着迷那些深邃的紫色,紫色常让不经意的生活变得神秘或者不寻常起来,它似乎是暗寂的黑夜里迷乱而憧憬的色彩,或者苦闷的日子里一闪而过的幽雅与悲伤。竹兰兰也是紫色的,她躺在一只竹编的筐子里,那是她延长了的摇篮,从出生,到现在,一直躺在里面。多数时间,她躺着不动,象吃饱了的婴儿。她的眼睛因为极度消瘦而大的吓人,睫毛又密又长,如果不是生病,也许是个漂亮孩子,但她的眼神始终暗淡无力,仿佛抬一下眼皮也要考虑半天,有一次,我钓了一只葫芦蛾,捏在手里,给她看,她抬眼看的时候,就象人们下一个巨大的决心,睫毛抖动着,眼皮瑟瑟索索地摊开,好容易看到她瞳孔里闪亮的光彩,她甚至想笑一笑,嘴角刚刚隆起,眼睛却忽闪一下,又闭上了,就象煤油灯被风吹灭那样突然。精神稍好一点的时候,她常时间地盯着一个地方看,没有人知道她看什么,有时候,感觉那双倦怠的眼睛是画上去的,美丽,却了无生气,还有她干枯的身体,象一多枯萎的牵牛花,带着死亡的神态,有一回,我听到她在沉默了半天以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听起来,就象一个对生命厌倦至极的老人一样,那时,她刚刚八岁,也许,她一出生,就已经不耐烦了,却不声不响地忍耐了八年。
秋天,梧桐叶落的季节,南园即使被树木簇拥,也一天凉似一天。杨树叶子象雨点一样纷纷扬扬地飘落,夏天,我喜欢在杨树下乘凉,风掠过杨树林,沙沙声仿佛来自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很多记忆仿佛被人从天空抛下来,那样的时刻,人就有隔然世外的感觉,内心有一点甜丝丝的凄凉感,裹紧毯子的时候,身体就象一只被风带走的种子。除了照看竹兰兰,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收集梧桐叶,以备冬天生火炉的时候用。梧桐叶带给我许多朴实又宽厚的印象,象又老又善良的老人的手,摸上去都暖融融的喜人,我常常捡到一小堆,就偷着点火把它们烧掉,呼腾腾的火苗多么暖和,又充满难言的兴奋,和略微的罪恶快感,竹兰兰见我点火,脸上布满忧愁,那表情就象我的母亲一样,她说,“二哥,你老是耍火,晚上又要尿炕了。”
攀上西墙,就看到西岭大道,大人都在大道西面干活,汽车南来北往,我厌透了竹兰兰,她象一根绳索,把我捆在南园,否则,我就可以坐在西岭大道上,坐上一整天,看汽车。那时,我老期望着某件了不起的货物从车上遗落下来,刚好落在我的脚旁,又没有人和我抢,我一遍一遍地设想这样的情形,也许是一只木盒,或者裹得很紧的布袋,我把它藏进路旁的草丛中,到天黑再打开,里面是一件我从没见过的东西,有着古怪的形状,它的用途最好谁也猜不出,我把它收藏起来,研究一辈子。然而此刻,我只能守着竹兰兰,忍受她艰难的眼神,看着她象鱼那样喘息,或者听她一遍一遍地这样请求我,“二哥,你把我再往火边挪一挪,我浑身冷透了。”
村子里静极了,墙角的母鸡“咕咕”地叫两声,可以让人吃一惊,好象世界一直停顿着,又突然启动一样。很远处,不知什么人家的风箱断断续续地拉动,或者门被风摇摆,在干涩的门轴中咯咯咯地响,又一阵风掠过,杨树叶子沙---地撒下来,落了竹兰兰一身。我一瞬间怜惜起她,这样孤苦无助,没有人在意她的痛苦,她惧怕一切,声响,亮光,凉风,孤独,黑暗,她这样软弱,一只母鸡都可以来到她的栖身的竹筐旁边,用冷漠的眼神把她端详一会儿,然后,高傲地转身离开。当苍蝇落到她的脸上,她甚至没有力气把它们赶跑,大人说,人快死的时候,苍蝇能闻见气味,会一群一群地赶过来,竹兰兰也快死了,苍蝇常常落在她脸上,半天都不飞走。我把竹兰兰移到火堆旁边,喂她喝了水,又用湿布擦了她的脸,真的,竹兰兰是个漂亮孩子,她用暗淡的目光看我,里面有对我的依赖,那年我也八岁,竹兰兰是我的双胞胎妹妹,我们相伴着来到人间,我掠夺了很多本来属于我们共同平分的资源,结果我胜利了,又健康又无赖,她却永远停止了生长。那天,在我家的南园,在经历了漫长的百无聊赖的时光和没头没尾的空想以后,秋风让我们冷得发抖,然而要一直等到日落,大人才会从工地返回,我靠烧梧桐叶为竹兰兰取暖,又摘了一大把牵牛花插在她的头发中,竹兰兰却丝毫没有快乐的样子,她满脸愁苦,你永远也想象不出一个八岁的孩子愁苦的模样,她反来复去地对我说,“二哥,你这回要是再打一个碗,咱妈非打死你不可。”
竹兰兰死于那年初冬,葬在西岭大道旁边的乱坟岗,她的小棺材象一只手提箱那么大,父亲把它捆在自行车的后坐上,以前带她去医院,父亲也用同样的方法,把那只竹筐捆在自行车上带走,不过这次,父推着空车回来了。
相关内容
| 

 团队博客
团队博客 锐写作
锐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