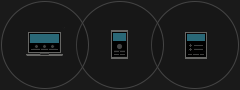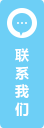|
南方之一 . 行走
作者: 35公里
|
发布: 2007/9/10 (17:05)
|
阅读: 33118
|
评论: 0
|
静态地址
|
内容源码
1.
体力恢复以后,我又可以长距离地散步了。在南方,冬天是最好的季节,那些依然绿色的植物,有一种属于冬天的静穆的美。自从医生认为我的鼻子有些花粉过敏以来,我就不敢轻易地悲秋了,所以,冬天不仅气候宜人,而且十分安全。其实,即使鼻子没事(事实上我一直怀疑医生是误诊),我也不怎么喜欢花。尤其在南方,花一律地肥硕并且妖冶,在山里见到木棉花,同行的人纷纷赞不绝口,我却抱着独特的审美不以为然,这么呆厚又充满肉欲的花,象花之地主者也,它落到地上的情形,就象一个人从楼顶栽下来,我看到有人将这些花串成串,挂在自家的阳台上风干,象风干一串辣肉。在北方,初春也见过玉兰花,似乎是一夜间就开满整棵玉兰树,颜色是塑料一样的白,那样肥大,突兀,令人不解,仿佛是对季节的一个玩笑,又象一个令人不快的仪式,发着蛊惑的气味。记起来了,我喜爱的是迎春花,那些纤细可怜的小花,就象初春一样孤清,在冷风中看到迎春花,感觉春天比想象力来得更早。
突然想起我的朋友L,她养了满阳台的花,其中一盆吊兰说好了是送给我的,我说,你替我养着吧,其实我从来没见过那盆花,那盆花就象互连网一样虚无,吊兰可以治疗消化不良,好象有一次我说自己消化不好,她便把那盆吊兰划归我的名下了。我不喜欢养花,是因为不喜欢同花争夺阳台这片读书空间,有一次,我见到母亲在厨房的窗外养了一盆吊兰,我立刻想起母亲是爱花的,老家的院子里,水井旁边四季都开着月季,西墙上是五颜六色的太阳花,她还试图种石竹却失败了,春天,她把苹果花插在瓶子里,用水养着可以开十天,苹果花的气味让人觉得艰苦年代的春天充满平实的,可以把握的幸福,母亲刚搬进我的新居时,常常从早市买回一些俗艳无比的塑料花,摆在桌上,喜滋滋地让我看,都被我偷偷扔掉了。我问母亲是不是想养花,她摇摇头说,是用来治病的,这句话让我非常悲伤,母亲突然间就老了,转眼就失去了那些小小的热情。
这里有一条漫长的海岸线,可以步行穿过的,有几十公里,我常常要走整整一个下午,亚热带的海风炙热又猛烈,走过码头附近的荒滩,见到没膝的野草地,开在路旁的紫色的蒲公英,一边是轰隆隆的建筑工地,一边是锈迹班驳的码头,有时候我特别想看泊在锚地的铁壳船,洋铁红的锈色,五彩斑斓的水面,还有泼墨一样的海风的幻觉,很象法国印象主义时期的油画。我喜欢耽于回忆,因为往往从回忆中捕捉到当时还有些模糊的心情突然变得清晰而且迫切。比如,那个边防哨卡,面容朴实的边防士兵,我经过时他脸上戒备又迷茫的神情,比如那个小岛,通过一座水泥桥与陆地相连,一踏上去,满目是在热风里倒伏而静谧的软草,比如满耳的风声,皮肤晒得滚烫,我想象自己的脸色,象高更笔下的塔稀提人,每想到这些,心头就涌起一种饱含热带色彩的印象,感觉到自然的生机,饱满与肆意,就一遍一遍想起德彪西的钢琴,仿佛漫山遍野的草荚在疾风中摇摆爆裂,也想起凡高的画,被太阳烘烤而扭曲的大地。
活着是件美好又无奈的事,因为醉心于一些不期而遇的快乐,便期望这样的事重复,但上帝每次赐予的是新鲜的快乐,这样做是不希望人贪心,有一次牧师对我说,祷告的时候,要请求上帝按他的意愿给,不要按我们的意愿要。下午,大约要到两点钟,才吃午饭,最喜欢一家干净而别致的小饭馆,几杯凉啤酒带来的清薄的醉意,可以无限延长这个下午,吊扇吹下的热风感觉象一个寂寞的小镇,孤零零的大街,懒散的居民,汽车载着游客从街上经过,留下一声汽笛,象一件遗落的包裹,一个小广场,四面是商店,旅馆,门诊部和车站,站在广场上咳嗽一声,传来很多回音,“啊呵”,这是游历西部时的记忆。有时候,太热的天,小饭馆就关上玻璃门,打开冷气机,当凉气冲散额头的汗水,突然就想起北方的秋天,孤清而落寞,尖锐而高远。想起一个秋夜的后半夜,老家的小院与围墙,墙上枯死的藤萝,躺在躺椅上听短波收音机,世界仿佛被冻成一滴露水,从收音机里滴落下来,漫天的星斗,俏皮的,肤浅的,阴险的,清高的。晴好的秋夜,在乡下,你差不多可以收到全世界所有的电台,听到各种古怪的方言,有那么一个时期,我痴迷短波收音机,调台的时候,仿佛从储物箱中翻检旧时的藏品,随着时间,地点,方向的改变,电台也不断改变,有时候,一个电台也象一朵秋天的蒲公英一样飘走了,再也找不回来。
回忆是件迷人的事,因为回忆的同时,上帝也让我们忘掉许多无聊的细节,所以记忆下来的,就象酿成的酒,有醉人的香甜。博尔赫斯《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的富内斯,记得住过去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的任何细节,他的一生,被这样清晰而庞大的记忆折磨 -- “富内斯仰面躺在床上,在黑暗中思索着他周围房屋的每一条裂罅和画线” -- 真是件可怕的事。
2.
我终于知道自己是个因循守旧的人,遇到岔路,潜意识中会选择曾经走过的那条。M是个极小的城市,步行一个小时,可以穿过它的大部,这里的街道细密如蛛网,所以,穿过M有无数种走法,但两年来我只走一条路线,查过地图,才发现这条路线十分古怪,至于当初为什么这么走,却记不清了。奇怪的是,即使我故意避开,拐进另一条巷,希冀着一点惊喜,就象天天盼着自己的生活会突然改变,然而几分钟以后,旧路又横在眼前,只是从新路口冷不丁来到一个熟悉的地方,会有完全陌生的感觉,我起初便以为找到了新路线,等到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已经沿着老路往回走了,这显得很滑稽,你对一个地方越熟悉,越摆脱不了一些魔咒一样的陈习。如果你住在一个地方超过两年,就有把它走遍的愿望。空闲时间,我把这个当作自己的事业,走得久了,就有逐渐掌握了一个城市的底细的感觉,说起来难以置信,许多标在地图的地方,实际上根本找不到,它们就象已经死去却忘记注销户口的人,也很少有人提及,地图是个浪漫主义者,很多象地图一样浪漫的旅行者吃尽了苦头,比如,地图上,这里的海岸线是条连续的弧线,但实际的情况是,你的行程会被许多莫名其妙的断桥,荒滩,废码头,沟渠或者破旧房子隔断而一筹莫展。忽然记起小时候去崂山的事。那时南望崂山,终日云雾缭绕,便以为是龙与神话的故乡,盼望有一日到山里去,路线在我看来根本不成问题,可以一直向南走,只要方向不错,早晚能走到那里。有一天,因为天气异常晴朗,忽然发现崂山其实离我很近,仿佛伸手就可以摸到,我便立即开始了去崂山的旅程,我的热情只维持了十分钟,我发现我甚至过不了眼前的那条河,要过河,我必须向相反的方向走很半天找一座桥。
我想了很久,准备徒步翻越M两岛之间的跨海大桥,在晚上。我在大雾的晚上拍过它的照片,起伏的桥身在夜空下,象一只翻飞着消失在大海中的炮竹,又象一个伸向大海深处的梦幻。虽然它的另一端连着陆地,当它逐渐在海雾中消失的时候,那情景依然令人惊讶,我想象自己的行程,随着桥身起伏,下面是被珠江染黄了的大海,从车上往下看,常有如堕深崖的感觉,然而夜晚和雾色淹没了恐高症与这座城市的礼节,我轻轻松松的走在天空与大海之间,这段路程十分漫长,便产生了没有尽头的错觉,仿佛自己随时会融化在氤氲中,或者从这座坚实的,用亿万吨水泥浇注而成,却象梦想一样轻盈的大桥上走失。
相关内容
| 

 团队博客
团队博客 锐写作
锐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