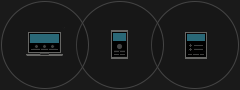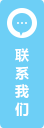|
南方之一 . 行走
作者: 35公里
|
發布: 2007/9/10 (下午 05:05)
|
閱讀: 22645
|
評論: 0
|
靜態地址
|
內容源碼
1.
體力恢復以后,我又可以長距離地散步了。在南方,冬天是最好的季節,那些依然綠色的植物,有一種屬于冬天的靜穆的美。自從醫生認為我的鼻子有些花粉過敏以來,我就不敢輕易地悲秋了,所以,冬天不僅氣候宜人,而且十分安全。其實,即使鼻子沒事(事實上我一直懷疑醫生是誤診),我也不怎么喜歡花。尤其在南方,花一律地肥碩并且妖冶,在山里見到木棉花,同行的人紛紛贊不絕口,我卻抱著獨特的審美不以為然,這么呆厚又充滿肉欲的花,象花之地主者也,它落到地上的情形,就象一個人從樓頂栽下來,我看到有人將這些花串成串,掛在自家的陽臺上風干,象風干一串辣肉。在北方,初春也見過玉蘭花,似乎是一夜間就開滿整棵玉蘭樹,顏色是塑料一樣的白,那樣肥大,突兀,令人不解,仿佛是對季節的一個玩笑,又象一個令人不快的儀式,發著蠱惑的氣味。記起來了,我喜愛的是迎春花,那些纖細可憐的小花,就象初春一樣孤清,在冷風中看到迎春花,感覺春天比想象力來得更早。
突然想起我的朋友L,她養了滿陽臺的花,其中一盆吊蘭說好了是送給我的,我說,你替我養著吧,其實我從來沒見過那盆花,那盆花就象互連網一樣虛無,吊蘭可以治療消化不良,好象有一次我說自己消化不好,她便把那盆吊蘭劃歸我的名下了。我不喜歡養花,是因為不喜歡同花爭奪陽臺這片讀書空間,有一次,我見到母親在廚房的窗外養了一盆吊蘭,我立刻想起母親是愛花的,老家的院子里,水井旁邊四季都開著月季,西墻上是五顏六色的太陽花,她還試圖種石竹卻失敗了,春天,她把蘋果花插在瓶子里,用水養著可以開十天,蘋果花的氣味讓人覺得艱苦年代的春天充滿平實的,可以把握的幸福,母親剛搬進我的新居時,常常從早市買回一些俗艷無比的塑料花,擺在桌上,喜滋滋地讓我看,都被我偷偷扔掉了。我問母親是不是想養花,她搖搖頭說,是用來治病的,這句話讓我非常悲傷,母親突然間就老了,轉眼就失去了那些小小的熱情。
這里有一條漫長的海岸線,可以步行穿過的,有幾十公里,我常常要走整整一個下午,亞熱帶的海風炙熱又猛烈,走過碼頭附近的荒灘,見到沒膝的野草地,開在路旁的紫色的蒲公英,一邊是轟隆隆的建筑工地,一邊是銹跡班駁的碼頭,有時候我特別想看泊在錨地的鐵殼船,洋鐵紅的銹色,五彩斑斕的水面,還有潑墨一樣的海風的幻覺,很象法國印象主義時期的油畫。我喜歡耽于回憶,因為往往從回憶中捕捉到當時還有些模糊的心情突然變得清晰而且迫切。比如,那個邊防哨卡,面容樸實的邊防士兵,我經過時他臉上戒備又迷茫的神情,比如那個小島,通過一座水泥橋與陸地相連,一踏上去,滿目是在熱風里倒伏而靜謐的軟草,比如滿耳的風聲,皮膚曬得滾燙,我想象自己的臉色,象高更筆下的塔稀提人,每想到這些,心頭就涌起一種飽含熱帶色彩的印象,感覺到自然的生機,飽滿與肆意,就一遍一遍想起德彪西的鋼琴,仿佛漫山遍野的草莢在疾風中搖擺爆裂,也想起凡高的畫,被太陽烘烤而扭曲的大地。
活著是件美好又無奈的事,因為醉心于一些不期而遇的快樂,便期望這樣的事重復,但上帝每次賜予的是新鮮的快樂,這樣做是不希望人貪心,有一次牧師對我說,禱告的時候,要請求上帝按他的意愿給,不要按我們的意愿要。下午,大約要到兩點鐘,才吃午飯,最喜歡一家干凈而別致的小飯館,幾杯涼啤酒帶來的清薄的醉意,可以無限延長這個下午,吊扇吹下的熱風感覺象一個寂寞的小鎮,孤零零的大街,懶散的居民,汽車載著游客從街上經過,留下一聲汽笛,象一件遺落的包裹,一個小廣場,四面是商店,旅館,門診部和車站,站在廣場上咳嗽一聲,傳來很多回音,“啊呵”,這是游歷西部時的記憶。有時候,太熱的天,小飯館就關上玻璃門,打開冷氣機,當涼氣沖散額頭的汗水,突然就想起北方的秋天,孤清而落寞,尖銳而高遠。想起一個秋夜的后半夜,老家的小院與圍墻,墻上枯死的藤蘿,躺在躺椅上聽短波收音機,世界仿佛被凍成一滴露水,從收音機里滴落下來,漫天的星斗,俏皮的,膚淺的,陰險的,清高的。晴好的秋夜,在鄉下,你差不多可以收到全世界所有的電臺,聽到各種古怪的方言,有那么一個時期,我癡迷短波收音機,調臺的時候,仿佛從儲物箱中翻檢舊時的藏品,隨著時間,地點,方向的改變,電臺也不斷改變,有時候,一個電臺也象一朵秋天的蒲公英一樣飄走了,再也找不回來。
回憶是件迷人的事,因為回憶的同時,上帝也讓我們忘掉許多無聊的細節,所以記憶下來的,就象釀成的酒,有醉人的香甜。博爾赫斯《博聞強記的富內斯》中的富內斯,記得住過去所發生的任何一件事的任何細節,他的一生,被這樣清晰而龐大的記憶折磨 -- “富內斯仰面躺在床上,在黑暗中思索著他周圍房屋的每一條裂罅和畫線” -- 真是件可怕的事。
2.
我終于知道自己是個因循守舊的人,遇到岔路,潛意識中會選擇曾經走過的那條。M是個極小的城市,步行一個小時,可以穿過它的大部,這里的街道細密如蛛網,所以,穿過M有無數種走法,但兩年來我只走一條路線,查過地圖,才發現這條路線十分古怪,至于當初為什么這么走,卻記不清了。奇怪的是,即使我故意避開,拐進另一條巷,希冀著一點驚喜,就象天天盼著自己的生活會突然改變,然而幾分鐘以后,舊路又橫在眼前,只是從新路口冷不丁來到一個熟悉的地方,會有完全陌生的感覺,我起初便以為找到了新路線,等到意識到這一點,實際上已經沿著老路往回走了,這顯得很滑稽,你對一個地方越熟悉,越擺脫不了一些魔咒一樣的陳習。如果你住在一個地方超過兩年,就有把它走遍的愿望。空閑時間,我把這個當作自己的事業,走得久了,就有逐漸掌握了一個城市的底細的感覺,說起來難以置信,許多標在地圖的地方,實際上根本找不到,它們就象已經死去卻忘記注銷戶口的人,也很少有人提及,地圖是個浪漫主義者,很多象地圖一樣浪漫的旅行者吃盡了苦頭,比如,地圖上,這里的海岸線是條連續的弧線,但實際的情況是,你的行程會被許多莫名其妙的斷橋,荒灘,廢碼頭,溝渠或者破舊房子隔斷而一籌莫展。忽然記起小時候去嶗山的事。那時南望嶗山,終日云霧繚繞,便以為是龍與神話的故鄉,盼望有一日到山里去,路線在我看來根本不成問題,可以一直向南走,只要方向不錯,早晚能走到那里。有一天,因為天氣異常晴朗,忽然發現嶗山其實離我很近,仿佛伸手就可以摸到,我便立即開始了去嶗山的旅程,我的熱情只維持了十分鐘,我發現我甚至過不了眼前的那條河,要過河,我必須向相反的方向走很半天找一座橋。
我想了很久,準備徒步翻越M兩島之間的跨海大橋,在晚上。我在大霧的晚上拍過它的照片,起伏的橋身在夜空下,象一只翻飛著消失在大海中的炮竹,又象一個伸向大海深處的夢幻。雖然它的另一端連著陸地,當它逐漸在海霧中消失的時候,那情景依然令人驚訝,我想象自己的行程,隨著橋身起伏,下面是被珠江染黃了的大海,從車上往下看,常有如墮深崖的感覺,然而夜晚和霧色淹沒了恐高癥與這座城市的禮節,我輕輕松松的走在天空與大海之間,這段路程十分漫長,便產生了沒有盡頭的錯覺,仿佛自己隨時會融化在氤氳中,或者從這座堅實的,用億萬噸水泥澆注而成,卻象夢想一樣輕盈的大橋上走失。
相關內容
| 

 團隊博客
團隊博客 銳寫作
銳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