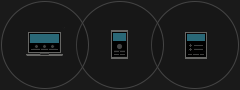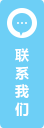|
南方之十二.物哀筆記之一
作者: its
|
發布: 2008/5/16 (上午 06:01)
|
閱讀: 59325
|
評論: 0
|
靜態地址
|
內容源碼
櫸林園
冬天的日子有時候是颼颼地過去,樹的葉子落完了,看不到風,海在遠處,看不到波紋,房瓦上有陽光,柿子樹上面的天空,麻雀一聳身飛出視線,洗藍的天空,有透明的蟲子一隱一現地游動,那是寂靜的人在視網膜上脫落的細胞。這些最冷的日子,風清澈而迅疾,仿佛“大雁銜著天空從窗外飛過”,冬天錚錚地響,又清澈,又堅硬;有時候緩慢地過,氣候暖洋洋,空氣中飛滿花粉一樣的顆粒,人打著呵欠,睡過一覺后,時鐘的分針只走了半圈,那個夢卻復雜得要命,幾乎有大半生那么長。櫸林園有數不清的山毛櫸,它們善良,溫暖又緘默,這是一片被遺棄的山林,無所事事的人才喜歡這里,坐在枯草中,眼睛望著某個方向,人的一生,有無數的等待,有時候僅僅是等待時間,在所有等待中,只有時間從來不會落空。園子里有個老人,他老得把整個世界都忘掉了,每次遇見他,都把我當成熟人,拉著我的手和我說話,他的臉上全是鼻涕,眼睛下方是兩道淚痕,粘滿了污垢,他對我說,從六八年到今,三十年了,這些年你都去了哪里,說完,便撇下我,一個人走開了。小時候,我喜愛又老又寬厚的事物,那里面包含著值得信賴的東西,我最好的朋友叫小黨,他的祖父八十歲,腰彎成九十度,他是那樣和善的一個老人,天冷的時候,我喜歡摸他冰涼的耳朵,他便把腿也彎下來,讓我摸。他在飼養院喂牲口,飼養院位于西嶺大道西側,我們叫做大屋,大屋前面有一片槐樹林,那里是麻雀的天堂。在我們全家準備遷往巴彥淖爾那年,老人在大屋前的槐樹林上吊死去了,那天,我去他那里討吃炒黃豆,他把口袋里剩下的全掏出來讓我吃,然后,對我說,你過來幫我個忙,說完,拿起一把杌子和一條繩子,領我進入槐樹林。他隨后對我說,我上去以后,你幫我把杌子搬走,然而就在我準備為他搬開杌子的時候,他自己一腳把杌子踢翻了。那天晚上,母親在槐樹林找到我的時候,我仍坐在那里吃著黃豆等他下來。母親當著小黨的父親詛咒那個老人,然而我當時一點也沒害怕。我常希望父親和母親也象他那么老,有他那樣軟弱的目光,父親卻總是把臉刮得鐵青,母親望著那張臉,眼里帶著妒忌,他們有數不清的事情可以爭吵,他們爭吵的時候,我就去大屋,悄悄地看馬吃草料。M的北海岸,有一條遭遺棄的老狗,它沿著海邊流浪,每走兩步,便停下來喘息半天,我中午在那里吃飯的時候,它走到我身邊,頭擱在椅上,眼睛望著我,不出聲,也不搖尾巴,我給它一點食物,它用鼻子嗅一嗅,便轉身走掉了。
人更多的時候,需要寂靜,寂靜是萬物的默契。櫸林園有數不清的小路,我已經記不清哪些是我走過的,路是大地的神經,越是細小的越敏感,小路的盡頭往往是一棵形狀怪異的大樹,一叢野花,一個能望見南海的山頭,有時候,什么也不是,它突然就終止了,有一些人就是這樣,他走路,懷著某種期待,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對自己說,就到這里吧,于是停下來,他并沒有疲倦,也沒有絕望,只是想停止,或者順著原路返回,很多次,我站在那里,耳朵里充滿簌簌下落的聲音,那不是樹葉,不是天籟,很多聲音,并不屬于什么東西,你聽到了,心里歡喜,這就夠了。晚秋的時候,橘紅的山毛櫸樹葉映著星星點點的天,天是那種蠱惑的藍,很多時候,人們說,藍色的天再也看不見了,其實并不是這樣,天最藍的時候,人幾乎有一種羞愧難當的感覺。九八年,是我留在Q的最后一年,那年,我異常迷戀格里高利素歌,每天傍晚都在櫸林園一直聽到山下亮起燈火,沿著山路下山,冬季的月亮象那些素歌一樣,清冷潔凈又遙遠,我從聲音和記憶中體味悲傷,人的悲傷,怎么和月亮相比。
冬至
一條蛇,游出小山谷,泉水冒著蒸氣,樹影布滿波紋,萬籟不驚,大地靜默,天從四面下垂,風靜止,云收斂,嬰兒停止啼哭,游子收起行杖,田野空洞,地氣上升,象萬箭穿空,巨大的水滴從天空劃落,如果有什么讓世界寂靜,讓男人酣睡,讓女人唱眠歌,是什么讓我如此不安,井水汩汩溢出,流星墜入山林,馬從草料中抬起腦袋,狗支起耳朵,空氣中是簌簌的墜落聲,當月亮即將從大海升起的時候,渴望去月亮旅行的人劃著船來到它身邊,那時,人和月亮的距離大約有一根桅桿那么高。
在月亮底下,漂浮著肥皂的氣味,白蛾緩慢地飛行,夜色沒完沒了,月季花安靜地開放,如果是夏天,空氣中就有一股昏昏欲睡的味道,春天,是清越,秋冬,是溫暖又悵惘,我的大伯,一個患了潔癖的單身男人,他每天都在這個時候,坐在院子里聽收音機,聽得全是些我不懂的民間大鼓戲,我常想,他肯定是個十分寂寞的人,僅僅想弄點聲音,打發他孤單的生活。他住的村子叫塔前,我一直覺得那里該有一座塔,但很多年來從未見過。我從小學校放學,到他那里,只有一里的路程,他央求父親,讓我去他那里住,我自己也樂意,小時候,總想抓住任何一點快樂。他為我做的飯十分難吃,餅硬得無從下口,吃過飯,他用兩個小紙袋,把自己的筷子頭包起來,放到座鐘上,也要求我那樣做,但我經常忘記,然后開始洗手,他總覺得手臟,用肥皂洗了再洗,他的手上終年都是腥腥的肥皂味。我成年后才知道,伯父患的是一種精神病,除了潔癖,還有輕度的受迫害狂,所以,他找我跟他一起住,其實是因為害怕。他的院墻上插滿了荊棘,門上了三道鎖,睡覺前,他攥起拳頭對我說,噓,別讓人聽見。除了這些,他剩下的熱情全放在了他的月季花上面,他伺弄的月季花無人能比,不僅常年開放,花朵也嬌艷,他最痛恨我把臟東西粘惹到月季花上,也絕不允許我掐他的花朵,花開了,就任它自然凋落,院子里終年就這么花木繚亂的。
有一年,一個民間曲藝團經過塔前,他們是一群貧困交加的藝人,靠四處流浪說書為生,中間有一個女子,見大伯每天都坐在最前面,目光熱切,還能和上幾句詞,便把大伯視為知音,又見大伯衣著整齊潔凈,不知不覺,竟暗生愛意,這些,都逃不出善良鄉人的眼睛,很快便有人開始為他們撮合,剛好女子早已厭倦四處漂泊,風雨不定的生活,欣然同意留下,于是,我忽然就有了個大伯母。因為這個緣故,我也不再去和他做伴,只是偶爾過去聽大伯母唱幾句大鼓,其實是想看個熱鬧,大伯結婚后,病奇跡般得好起來,拆掉了墻上的荊棘,還主動邀請鄰居來家聽唱。夏天,大家在他那個不大的小院里席地而坐,聽大伯母唱《黛玉葬花》,“孟夏園林草木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我只記得這么幾句了,大伯可句句都能背誦,他還有一整本的曲譜,全是整齊的毛筆小楷,有《大西廂》,《探晴雯》,我并沒聽過,或者,即使聽過,也忘了。為了養家,大伯每天去鎮上的窯場做苦工,聽父親講,大伯的變化非常驚人,一整天在窯場的爛泥坑滾爬,中午吃自己帶的紅薯,卻省下窯場發的饅頭帶回家給大伯母,他們家再也聞不到那些腥腥的肥皂味,但月季花依然開得艷麗。那時我已經去了萊陽讀中學,對大伯家的事漸漸沒了興趣,回家時,偶爾聽父親提起,也只是隨便那么一聽。又過了很多年,我忽然感覺似乎很久沒見到大伯母了,問母親,母親說,你還不知道?你媽姆給人要回去了。我吃了一驚,又覺得奇怪,不知道要回去是什么意思,母親便對我說,你媽姆本來是嫁了人的,婆家對她兇,就跟那幫戲子一起跑了,跟你塔前大爺一起過的時候,還沒離婚,人家婆家人找了幾年,到底找到這來了,去法院一告,就給人要回去了。“那我大爺呢?”我問,母親說,“病又犯了,你抽空也該去看看他。”
那天,我費了很大力氣,才叫開大伯父的門,他的小院子冷冷清清,麻雀在地上尋找谷粒,見到人,撲嚕一聲飛走了。月季花也枯死了,水井的旁邊顯得空空蕩蕩,在北方,人們習慣在水井的旁邊種點月季什么的,我想,沒來大伯家,總該有五六年了,那時,我還小,喜歡惹弄些花草,雖然大伯父呵斥,我還是把月季偷著掐下來,丟到井里,月季是帶著一點藥香的,那個味道一輩子也忘不掉。童年時的日子那么貧乏,人很容易對一些微不足道的東西傾注熱情,夏天,我們喜歡玩弄洋金花,把那些皺巴巴的花瓣撕下來,揉碎了抹到別人鼻子上,洋金花又叫曼佗羅,大約帶點致幻作用,但我并沒體驗過那種致幻的滋味。大伯見到我,說了句,回來了,便輕輕握了下我的手,握完后,一個人回到屋子,在臉盆里用肥皂洗手,他洗了足足有半個小時,洗完以后,從座鐘上取下一個紙包,打開是一條白毛巾,把手仔仔細細擦了一遍,又疊好,放回去。大伯去世之前,據說已經幾個月沒說一句話,彌留之際,忽然抓住父親的手,說,“兄弟,我走的時候,你可要仔細給我洗一洗啊。”
相關內容
| 

 團隊博客
團隊博客 銳寫作
銳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