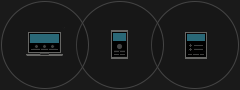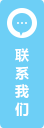|
南方之十.城市之二
作者: its
|
發布: 2008/2/11 (下午 02:53)
|
閱讀: 51908
|
評論: 0
|
靜態地址
|
內容源碼
如果地震臺預告明天有地震,G大得都讓人懶得逃走,黃曾經這樣描述G。這是一個早晨,我剛剛從G城的好睡眠中醒過來,窗外是一片樹林,地上滿是土灰色的樹葉,它們都是三四年前的落葉了,一直那么堆著。這很容易讓人忘記現在的季節。樹林中有一個不高的水泥屋子,沒有窗,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那是個什么建筑,這時,鳥喳喳地叫起來,也許它們早就叫了,只是我剛剛意識到。這大概是最好的境地了,破舊又偏僻,這樣的早晨,似乎被神遺忘了的一段好時光,有一種偷偷的喜悅。園子里沒有一個人,我很想進去走走,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植物悄無聲息,內心便有那么一種灰撲撲的快樂感,很多快樂,人匆匆就嘗試完了,如果不是曇花一現,多半也讓人事過之后心懷愧疚,惟獨這樣靜悄悄的暗喜才會持久,就象一條狗,叼著食物走到角落里去,獨自待上那么一會兒,有這么一會兒,也就心滿意足了。我滿心喜愛這里參天的古木,一整座園子,古紅色的老房子掩映其間,我自小喜歡高大和寬厚的東西,比如馬,樹,大山和身邊那些年長而老實的人。馬寬容,樹溫暖,大山,恒久而神秘,我曾經多少次在傍晚遠眺嶗山,繚繞山間的云象火一樣紅,太陽悠忽而謝的時刻也有無盡悲風侵透少年人的心。西墻外也曾有過一片樹林,生的是梧桐和臭椿,蟬脫殼的季節,每天可以在樹下揀到一口袋蟬蛻,賣到中藥站,一分錢一只,春天在林子里牧鵝,有一回,我追趕一只鵝的時候把它踩死了,這相當于創下一個大禍,天黑了,我坐在死鵝旁不敢回家,一個人,長著一張馬臉,又丑又高,他正在旁邊澆白菜,便走過來,撿起那只死鵝,說,還是只母的,然后,放回原處,嘆著氣走了。他實際是個傻子,至少村里人這么認為,我們叫他長云。他母親因為得了嚴重的角膜炎,眼睛周圍總是粘著眼屎,人們叫她日本娘們兒。他有一個哥哥,家里人費盡周折為他娶了媳婦,其實是拿她妹妹換的。結婚那天,很多人去鬧洞房,因為他們家這樣卑微,所有的鬧房人到頭來都極不尊重起來,事態幾乎失去控制,新娘已經開始掉淚,這時,長云出現了,手里拿著一根繩子,挽了個扣,套住為首的一個人的脖子,一聲不吭地把他勒了足足有一分鐘,那個人最終僥幸撿了條命,從此遠遠地見到長云便渾身發抖。長云放下我的死鵝走開后,我連一秒鐘都沒敢耽擱就跑著回家了。我突然想起這件事是因為這里的古木讓我想起西墻外的那片梧桐與臭椿雜生的樹林,內心象一盞燈那樣親切起來。長云在第二年的夏天死在南溝的水塘,一個收廢品的外地人在那里洗瓶子,不知怎的便落水了,長云聽到呼救,第一個趕到那里,一個猛子扎下去,頭扎在陳年的淤泥中,腳還露在水面上。
如果讓我選擇,我愿意活在夢的境地,把過去的夢整理一下,發現那是個完整的四維世界,從一個夢境進入另一個,你不必考慮時間,我常常夢見十年前夢見的一個地方,也會把當時中斷的情節繼續下去,比如曾有一座入云的山,上山的路,卻是幼年時常走的一條鄉路,我一邊走一邊想,山那邊就是北冰洋,最后的情節就不記得了。左晚莫名其妙地夢見了北冰洋,水是冰冰的藍,我忽然想起了那座山,果然還在,便從山頂下來,走到一個地方,我對自己說,當時那個夢,就是從這里斷的。我還夢見過一個地方,也是冰冰藍的水面,但當時并沒覺得是北冰洋,現在想來,那兩個畫面是一模一樣的。在那個夢里,我在結了冰的水面行走,冰一直嘎嘎地響,我便安慰自己說,別怕,人是永遠都不會夢見自己死去的。
上次來G是陪著D,天一直陰沉著,我們慢騰騰地走,G這個龐然大物,每天有一千萬人在里面分贓,如果你帶著異鄉人的面孔,上街,加入到隊伍,把這個叫做生活,或者娛樂,你就有被分掉的危險,所以,在G,我從沒真正歡樂過,一千萬人在街上毫無頭緒地爭奪時間,你就象在臺風眼支起一把躺椅,我不只一次地沿著地圖穿過G,這是步行者最難征服的一個地方,你要同汽車,小偷,二癢化碳和更多快腿的人賽跑,所以,盡管我早已習慣用散步消磨時光,在G,我們只好鉆進汽車,從一個站逃向另外一個站,聽滿街的人嗡嗡地響,看計價器象點鈔機那樣跳動,我們頻繁地查看時間,從巴士的站牌上讀站名,我們就這樣在兩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一起談愛情。D說,從火車東站到西郎,全程六元,我們只買了兩元的單程票。于是,D驚慌起來,這是個極度愛面子的城市,但我們忽然愛上了這個地方的地鐵系統,它躲在地下,有涼爽的風,除了鐵軌的聲音,剩下的就是寂靜,當我們鉆入地道,象一對鼴鼠,忘記時間,太陽,和復雜的生活,我們相互偎依,取暖,談話,看著對方的眼睛,我們終于看到了G的愛情,全長三十六公里,攝氏二十度,很多年以后,還會懷念那一天,在地下五十米,擁抱著D。當我們返回地面,我們已經累計欠下地鐵公司二十元的票款,但沒有人知道這些,我們用一個小時,加上愛情,Hack了G城地鐵的收費系統。
“你已經一動不動地站在這里一個小時了。”黃對我說。
“我在看這個園子”,我說,“又想起了老家的那個林子和許多亂糟糟的往事。”
“今天,你好好出去轉一轉吧,這個季節,G說起來,還是挺熱鬧的一個地方。”黃這樣建議我說。
我卻一瞬間灰懶起來,覺得G不過如此,慕著名去看一個地方是件無趣的事,而且人的一生,總有無數際遇是無意中得到的,比如九六年在拉薩,一路顛簸了幾千公里,我卻很快把那些偉大的風景淡忘了,大昭寺,八角街,布達拉宮還有滾滾的拉薩河,最想念的,卻是西藏日報社的招待所,那個小小的院落,肥手肥腳的女管理員,接自來水的石頭臺子,房檐下一溜花花綠綠的臉盆。每天傍晚,我買來啤酒坐在那里喝,覺得悄悄寂寂的生活有一股容易承受的甜蜜,或者說,幸福,就是你恰好需要幸福的時候遇見的任何一件事。所以,我對黃說,“我實在懶得出去,如果不打攪您,就在這里待一會兒吧”。
“你這個奇怪的孩子,”黃說,“你乘了兩個小時的車來到G,又步行三十公里找到這里,就是為了在這個草木繚亂的地方陪我發愣。”
“九六年在拉薩,”我說,“在西藏日報社的招待所,我遇見了一個同鄉。他待在那里已經六年了,我們見面的第一天,他就約我喝酒,對我講他的事,說他怎樣厭惡回家,怎樣搪塞自己的妻子,怎樣和野女人私奔,怎樣做蟲草生意卻沒賺到一分錢,他一點也不悲傷,也不后悔,始終笑嘻嘻的,象講別人的故事。然后他向我借錢,我一點也沒猶豫就借給了他,誰知在回招待所的路上,他又莫名其妙地把錢還我了。”
"小時候,"我接著說,“冬天,我渾身冷得發抖。出太陽的日子,十字街的墻腳,一群老頭兒,披著大棉襖,蹲在那里曬太陽,我羨慕得要命,想,趕緊快點變老吧,就可以和他們一起,瞇者著眼,過那等好日子。人經常有一些奇怪的愿望,我母親曾對我說,她最想的,是坐在山頭上,吹著涼風,看太陽落下地平線山。每次想起這些,心里總有些發酸。你肯定奇怪我為什么說這些沒頭沒腦的話,我也奇怪。你知道,我每天的生活,非常狹窄,幾乎不需要我去選擇,任何事情都象注定的一樣,我常想,為什么M的生活這樣單一,老人坐在窗口發呆,孩子頂著黃頭發看漫畫,其余的人,都待在一個他最痛恨的地方盼著下班。就連在充滿胡思亂想的G,也是一樣,我豈不知道這里有百年的騎樓,上好的烤鵝,緩慢流淌的珠江水和一北京路的漂亮女孩,但我總想等待一些愿望出其不意地從記憶中跳出來,然后看看眼前的生活,它是否是某個愿望的延續。”
我這樣說著的時候,黃阿姨已經倒在她的躺椅中沉沉地睡著了。她后來在給我電話中,一邊埋怨我的不辭而別,一邊抱歉自己的失禮。接著,她對我說,“不過,那天,我真的睡了個很香甜的好覺,夢見了許多有趣的事情,一開始,你說的那些話,我覺得有些煩,在G,沒有人會花二十年去記住一個愿望,可我又想,有一些愿望,可能你并不是真想實現。另外,你的那個 D ,她現在是否有什么消息了?”我說,“有,但她的事,在電話里三言兩語是說不清的。”
相關內容
| 

 團隊博客
團隊博客 銳寫作
銳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