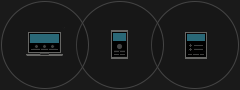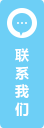|
南方之九 . 居住地
作者: its
|
發布: 2008/1/11 (下午 02:47)
|
閱讀: 52510
|
評論: 0
|
靜態地址
|
內容源碼
此行的目的,我對母親說,是回去看看兒時的居住地。居住地?母親望著我,臉上帶著疑問。其實,就是出去轉轉,我趕緊說。母親笑了,說,五十年前,你祖父說出去轉轉,結果就在那里留下了,三十年前,你父親也出去轉轉,后來我們全家人都跟著去了,你們都是些怪人,我一輩子都不想那個地方,我什么地方都不想,除了自己的家。媽,我問,我想知道,當時我們走的那天,是不是十五,我老記著那晚是滿月,五叔推著我,我們沿西嶺大道去火車站,我現在一想起來,就滿腦子的月亮在眼前晃。母親回答說,是初六吧,五月初六,端午節的第二天。
很多年來,每次旅行,動身的前一天,我總忍不住和母親談一會兒,成年的男人用這種方式迷戀母親,是件足令人羞愧的事,但旅行常勾起我心中離別的苦愁,覺得只有她才最理解這些,這大概就是少年時代的游歷生涯在內心留下的痕跡。晚上從她那里回來,照例睡不著,便盼著早點上火車,想著一個人在路上的快樂,很多時候,快樂就是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把自己忘掉,或者在遙遠的異鄉,隨便想念點什么,而且我是這樣喜愛火車,沉重的玻璃窗被兩個人抬起來,干熱的風灌滿耳朵,遠山,彎曲的河,還有沒完沒了的大平原,在這種時候,我甚至喜愛一些乏味的風景,透著那么一種寂寞味道,火車把旅行無限拉長,長到你不覺生出厭倦,最好的旅行就是含著厭倦,否則你永遠都不會想念那些走過的路,還有,那些穿過秋野的搖擺夜晚,是我多年來最可靠的夢境。
母親說是五月初六,那么,當時還是B的夏天,我們到達住地已經是深夜,那是一次奇異的旅行,傍晚出發,在深夜到達,我在火車上一共三天三夜的記憶,如今全然丟失了,那種感覺就象五叔直接用手推車把我們推到了目的地。那時,我從車上跳下來,周圍是令人心悸的黑暗,象深不可測又充滿陰險的水井,我需要仰起頭,看著漫天的星星才站得穩。星星也讓我內心感到塌實,五歲的時候,我已經熟悉了北半球星空大體的模樣,那是夏夜在打麥場睡覺的收獲,我還得過夢游癥,睡到半夜,一個人走開,沿著打麥場的小路往家走,家里的大人常常在凌晨發現我睡在另一個打麥場的麥草堆里,這不值得大驚小怪,那時我并不害怕,卻把家人嚇壞了,他們說我的魂拴不牢,便把我關在家里睡,我依舊夢游,突然醒來后,看著黑漆漆的屋頂,驚恐得把衣服都尿透了。家人總想讓我明白家里才安全,但在我看來,那個擺著水泥大甕,有三個地窖,四個房間,塞滿破爛柜子和祖傳的器具的屋子才真正可怕,在打麥場,天上熱熱鬧鬧,足足有一千萬顆星星在說笑,它們的事情我早就熟悉了,如果大人也知道天上的星星每晚都吵吵嚷嚷些什么的話,他們準忍不住笑出聲來。來到B的第一個晚上,我用極快的速度掃了一眼星空,心一下子安靜下來,當母親說她已經完全掉了向的時候,我用手指著北斗七星說,那是北。現在,火車就朝著北斗星的方向開,山西已經過去了,我睡不著,莫名其妙地激動著,風從窗的縫隙灌進來,那是一種怎樣的涼!讓人忽然渾身充滿力氣,覺得身體是可愛的,它如此舒暢,象一種氣味,迅速融化在空氣與夜色里,記憶在一瞬間打開,我從沒想到,自己的內心突然會涌起這么甜美的東西,在冰涼的青草的氣味里,象種子逢著了雨水,如果沒有雨水,種子的記憶就化作了泥土,我的記憶,有一天將化作清煙,但這一點也不令我傷感,我想,此行是值得的,不管為了什么,至少,我的身體,它一直被莫名的疲倦與郁悶所累,從冰啤酒與睡眠中尋找出路,我也厭倦了它,覺得它阻礙了我的快樂,但我在這樣一個凌晨,坐在火車的玻璃窗旁邊進入內蒙古,最先在快樂中蘇醒的的,是我的身體。
祖父的小牧場的北面,有一條河,后來我才知道那就是烏加河。烏加河水泛濫的時候,形成一片浩淼的沼澤地,夏天被蘆葦覆蓋,冬天蘆葦倒伏,露出零星的冰原。B只有夏天和冬天兩個季節,而且夏天總是匆匆地就過去了,太陽最毒的日子,蘆葦綠得發黑,讓人覺得它們在狠狠地長,然而只消一夜北風,它們就悄無聲息地枯敗了,枯掉的蘆葦地,從遠出看,有四五歲的孩子所想象的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大群的水鳥飛進去,我經常在窗口的寒風中瑟瑟地趴著,看它們從北方的天空飛下來,成片成片地落在里面。祖父說,一整個冬天,它們就在里面過冬。我趴在北窗上,眺望蘆葦地,心里滿懷著渴望,希望有一天走進去,看看那個鳥的國家,在我的想象中,它們這樣睡覺,每一群都圍成一個圓圈,一個枕著另一個脖子,就象一群羊那樣,互相取暖,這個想象把我迷住了,羊這樣曬太陽的時候,我便擠到它們中間,從它們身上取暖,B的冬天直通通地冷,不過,沒來B之前,到了冬天,我身上也這么冷。我趴在北窗時間久了,祖父就走過來,問,你老這么看,看什么呢?我沒有辦法告訴他,我在祖父面前異常地害羞,雖然認識他已經幾個月了,每次看到他,心里總是驚慌失措。祖父說,從窗上下來吧,我們今天要把它糊起來,因為西伯利亞的寒流就要來了。我忍不住打了寒戰,西伯利亞,這是個陌生而古怪的字眼,但一聽到它,我的渾身立刻涼透了。西伯利亞寒流到來后的一個日子,祖父終于帶我去了蘆葦地,祖父說,只有冬天,沼澤地凍硬了,才可以進來,夏天這里根本沒有路。祖父是去收集鳥的絨毛,他要用這些絨毛為我絮一雙暖和的靴子,我穿上它以后,世界立刻變成暖融融的樂土,才知道自己每天都冷得發抖的原因是腳冷。在那片深不可測的沼澤地走了一天,我沒有見到一只鳥,更沒有象期待的那樣,看它們擠在一起睡覺,我人生的幻滅感多半來自這樣的兒時經歷,這真令人難過。
在B,我現在沒有一個熟人,即使他們小時候見過我,也斷然不會把眼前這個行跡可疑的外鄉人跟兒時的我聯系起來,為了讓自己的出現不至于那么突兀,我假稱自己是地質隊員,前來勘測烏加河的流量。然而地質隊員接著就犯了一個低級的錯誤,我站在一條小水溝的旁邊,向人們打聽去烏加河B段的方向,他們用西北農民最善良的表情嘲笑了我一下,說,這就是。我吃了一驚,問道,很多年前,這里有一片蘆葦地。他們又笑了,“外鄉人”,他們說,“這里沒有蘆葦,這里草也沒有,光有沙”。我開始懷疑自己行程的準確了,火車過了山西,進入內蒙,呼和浩特,包頭,五原,路線是背熟了的,我坐在窗口,看了一路的大青山,從地圖上,我找到了兒時所眺望的狼山在陰山的位置,從五原下火車,乘汽車到什巴,徒步穿過一塊十里見方的沙化地,B就在眼前,然而眼前的B已經沒有絲毫記憶中的模樣,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裝下去了,否則,我最好轉身離開,沿著原路返回,然后,把這件事忘掉。所以,我便向那幾個村民中年歲稍大說了這些話,
“你們也許不記得我了,大約三十年前,我住在這里,你們至少認得我的祖父,他住在蘆葦地的南邊,有一塊小牧場,他的名字叫劉風錫,從口里來”
“那么,你們老家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一個老人說,“那些年間,有不少口里的人來逃難,說老家發大水,劉風錫我不認得,你們認得不?”他轉身看著其他人,其他人都茫然地搖頭,在那一霎那,我決定離開,心里也為自己的無趣感到惱怒,天快黑了,如果湊巧,還可以在天黑前趕上最后一班汽車,返回五原。我開始想念某個五原縣城內的小旅館,二層樓的小房子,房前是布滿灰塵的樹,四周這么靜悄悄的,年輕人騎著自行車,車把上掛著叮當的飯盒,他們要去工廠上夜班,而我,坐在一片孤寂的異鄉的夜色里,喝著啤酒,或者,隨便看看天。
我第二次回去看B的時候,找到了不少還記得我的人,他們很驚訝我居然這么大了,在他們的眼里,我應該還是那個又瘦又弱的小孩,穿著不合身的衣服,在冬天,抄著袖子,在街上走來走去,不說話,也不笑。
“你還記得吧”,三爺爺說,他曾經是祖父最好的朋友,“有一年冬天,你差點死了。”
“真的?”我感到很驚訝。
“那年,我趕著馬車去狼山拉煤,你死活要跟著去,你祖父就讓去了。”
“半路上,起了暴風雪,我趕著馬車,你坐在后面,冷得發抖,馬跑得飛快,也不知道跑了多久,我感覺你似乎在后面睡著了,就轉身看了一眼。”
“這一看把我嚇壞了,你在車上沒了。”
“我趕緊勒住馬。這么大的雪,要是你睡著了從車上顛下去,不用多久,就沒命了。”
“我趕緊順著車轍往回跑,一邊跑,一邊喊,一口氣跑了五里路,我想這回完了,回去跟你祖父怎么交代。”
“我把每個雪窟窿都找遍了,還是沒找到。”
“我沒了主意,煤也不想拉了,就往回走,找我的車,回到車那里,才發現你躺在地上,腳上纏著根繩子,躺在雪地里,還真睡著了,我把你叫醒,你楞了大半天才明白過事來。”
“那么”,我問,“我們最終去狼山了沒有?”
“去了,還拉了車煤回來。”
那一次回訪,我登上了狼山,根據三爺爺的說法,我這是第二次來,但第一次的事,包括那次歷險,都不記得了。狼山是陰山山脈眾多山峰的一個,從祖父屋子的北窗,視線離開那片蘆葦地,在北方云霧繚繞的地方,就是陰山,我認為那就是世界的盡頭,我問祖父是不是這樣,他說,也許是吧,但我立刻又不甘心起來,說,山的那邊,至少也該有點東西吧,他說,還是山,于是,我絞盡了腦汁想出了這樣的問題,有一天,我走到世界的盡頭,前面已經沒有路,無論怎么走,用腳,用船,用翅膀,都不能前進半步,那么擋住我的,到底是什么?
相關內容
| 

 團隊博客
團隊博客 銳寫作
銳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