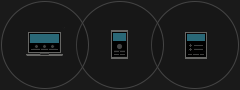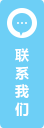|
南方之十三.山
作者: its
|
發布: 2008/7/24 (下午 09:22)
|
閱讀: 42554
|
評論: 0
|
靜態地址
|
內容源碼
山
D常說,她的家鄉有很多山,到了X,我才明白很多山是什么意思,象稻田里生出的一片樹林,一棵一棵拔地而起,塞滿人的眼睛,不象北方,北方的山總要經過綿延的醞釀,從平原,到丘陵,起伏縱橫,一座大山的方圓,常常有幾百公里,這里的山更象園子里的盆景,有些精致,清秀,一種象竹子那樣的清秀,象南方女子,細手細腳的,讓初見的人驚訝。山原本是一些深邃的地方,在西北,山只有石頭,一覽無余,但站在山里,人始終被一種悲郁的氣氛纏繞,仿佛靜寂的背后是世界的盡頭,在我的家鄉,山平和了一些,那是些世俗的山,寬厚,善良,被鄉人拿來作糧倉,柴房和石料場,從遠處看,遮住了半面天空,走近了,只是個小土坡,母親說,她平生最想做的,就是在山頂上找塊石頭,坐在那里看太陽落山,但小土坡的西面是一片比它還高的大嶺,象一匹從天際斜垂下來的幕布,太陽幾乎要沿著它滾落下來,我小的時候,以為大嶺的末端有一個坑,太陽就落到那里面去,常想過去看看,想象看到太陽躺在坑里的模樣,象一只巨大的柿子,我向它拋石頭,或者用繩子把它拖上來,然而直到今天我也找不到大嶺的盡頭,那只是一片傾斜的土地,是大地給眼睛的錯覺,冬天,西北風從大嶺以外卷著沙塵長驅直入,那些蜿蜒的小路幾乎象蛇皮一樣被風吹走,廣播站的電線,它們被架在涂了瀝青的木頭稈上,一個村莊連著一個村莊,電線的嗚咽聲令人膽寒,它發布的有關冬天的消息更令人戰栗,而晴好的日子,耳朵貼在電線桿上,可以聽到美妙的嗡嗡聲,我對大哥講,這就是電波的聲音。
D說,我才二十多一點,就覺得自己最好的時光已經過去了。小時候,我一直住在這里,你看到了,周圍全是山,父親在樓下的車站上班,我站在這里喊,“爸爸--”,周圍的山都回應“爸爸--”,我就對姐姐說,有人在學我,有一次,我數了數,回聲最多有十七次。現在,這里蓋滿了樓房,再也沒有回聲了。你現在還敢喊嗎?,我笑著問。不喊了,D說,但很想,很多次,我站在這里看著他,一套粘滿油污的工作服,維修的車來了,他立刻仰臥著鉆到地槽下面,我的心就緊張起來,擔心他再也不會鉆出來,有一次,我夢見一個人拿著軟皮膠管往地槽里面灌水,我哭著跑下樓,往地槽里面望,里面再也沒有了我的父親。小時候,我常常這樣哭著驚醒,父親聽到我哭,扔下手里的活,上樓來抱我看那些風景,這里的風景,看也看不完。我隨著D的目光向遠處看,這是個破爛的小縣城,位于山與田野的邊緣,一條河繞過半邊城,水是嫩嫩的綠,我猜想那里面長滿了魚草,南方雨水豐盈,河與周圍的土地連成一片沼澤,沼澤地里開滿粉藍色的蒲公英,也有白色的蘿卜花。
什么時候,我們去那里轉轉吧,我對 D 說。去不了的,那里根本沒有路,D 說,小時候,我沿著河走,希望找到河的盡頭,我一直懷疑河水來自一個山洞,因為一年四季,河水都是冰涼的,有一天,我自己沿河走了五里路,河邊的紅土又粘又滑,我心疼腳上的塑料涼鞋,就脫下來掛在脖子上,父親說,我小時候有些孤僻,只愛一個人玩,其實我只是想發現個巨大的秘密,討他歡心。從我記事開始,父親就不開心,但從沒責罵過我們,他愁悶的時候,就站在陽臺上,看著那些山,有時候一站就是兩個鐘頭。那天家里人找了我一整天,然后去派出所報了案,公安局的人在沼澤地找到我的時候,我還在那里艱難地跋涉。T,你別笑我,不知為什么,在回家前的那些日子,我老夢見這些事,有一天我夢見河的源頭是一個巨大的溶洞,我們打著火把進去了,在里面走啊走,我跟你說,壞了,怕是迷路了,你說不怕,我們就那樣走了半天,出去一看,山那邊居然是Z ,一想起這個夢,我就笑得要命,不過,如果這是真的,該多好。如果這樣,我就可以每個月都回來看我的父親了。你知道嗎,有一次,父親對我說,他就要失業了,我對他說,我可以養活你和媽媽,他對我慘淡地笑了一下,我父親今年剛好六十歲,五年前,他就應該退休的了。
我不曾知道,D的內心有這樣一些情感,她多數時間象個不諳世事的小女孩,對年長于她的,存著依賴心,她回到我身邊以后,忽然連做飯,也不會了,如果我不去,她便吃快餐面度日。我做得一手好菜,喜歡看她吃得滿頭是汗,但有時候,愛情又不免讓我空中樓閣起來,回家前,我曾想勸她和我一起去云南旅行,我對她說,我困在M快五年了,如果再不出一趟遠門,怕要活活悶死,她不愿意,說云南有的,她們家也有,比如山。于是在D的家鄉,我平生第一次見到這么密集而奇怪的山,就象多年前的一個夢境,一座園子,里面有很多山,每一座都象一棵樹那么大,我在夢中把它們伐倒,亙古綿延的秘密變成化石,雖然你永遠也摸不透一座山,即使它在你腳下,然而當山倒下,躺在你身邊,你覺得世界改變了,有一種偉大正在被你掌握的感覺,幸福象雨滴那樣收藏到瓶子里,鳳凰鳥落滿手臂,流星堆在屋檐下,月亮上垂下軟梯,而把太陽從碎石坑拖上來的感覺突然變得那樣平淡無奇。
那天,為了重溫一下D小時候的經歷,找到那條河的源頭,我和D在那些山間走了一個下午,最后,終于連河到底是往哪個方向流都糊涂起來,在現實中,這種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是很難的,河有無數的支流,每一條支流都可能把你引向困境,很難想象D在童年時代,有這樣的耐心,當年她身陷沼澤地的地方在直線上離她家只有五百米,但茂密的蒲公英和蘆葦肯定遮住了她的視線,如今,這里的蒲公英依然茂盛,如果不仔細看,你不會明白蒲公英是這樣美麗的花,它們在風中搖擺的樣子顯得稚氣十足,散發的藥香帶著苦清的味道,我想,春天,即使在濕潤的南方也是顯而易見的事,而我記憶中的春天是干燥而堅硬的,它只是一些細微的氣味,被多夢而惶惑的睡眠放大,等著滿耳的風聲停息,等著一些事情發生,然而除了零星的回憶,你什么也等不到,夏天轟隆一聲就來了。
我對D說,我們家的東邊大約十里,有一片海叫丁字灣,從西嶺大道上,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水,那里有座山,叫五龍山,我常想,站在五龍山頂看丁字灣,該是多么驚心動魄的事,便一直想去看看。終于有一天下午,我騎著自行車去了,那段路并不遠,卻走了一整個下午,因為那些綿延縱橫的鄉間小路就和這條河的支流一樣多。到了五龍山,天色就晚了,山上響著松濤,山那邊的丁字灣或許正是鋪天蓋地的一片大水,我卻無論如何也不敢上山了,在那里猶豫了半天,只好掉轉車頭就往回趕,心里十分害怕,等到了家,又開始后悔,其實我后來知道,從五龍山上根本看不到丁字灣,走近了,丁字灣只是一片一望無際的灘涂,人們在灘涂里建蝦池,我兒時的一個伙伴,我叫他春左,后來就在那些蝦池做工時淹死了。蝦池很深嗎?D問。我說,其實只有他的腰那么深,他劃著船在里面喂蝦,不知怎么就掉下去淹死了。你知道嗎?他是個很機靈的人,小小的個頭,比我矮一頭,喜歡跟我玩,夏天,我去他家的瓜地幫他看瓜,瓜熟了,從瓜蒂上脫落下來,我就跟他說,咱吃吧,都掉了,他趕緊說,晚上它們還要長上去的。那個時候的小孩子把友誼看得那么重,如果有人欺負他,我可以豁出命和人家打架的。可是,有一次,他做了一件讓我驚訝了很多天的事,我們便從此決裂了。我們的學校里,有一個美術老師,模樣兇狠,又剃了個光頭,我們都怕他,有一次,他從我們身邊走過,春左忍不住罵了一句,小和尚,聲音雖然不大,這個每日里都悶悶不樂的年輕人卻清清楚楚地聽見了,他象突然想起了什么要緊事那樣咯噔一下站住了,拿手摩挲著自己的腦袋想了一會兒,然后轉過身,一聲不吭地向我們走來。春左和我都嚇呆了,那時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趕緊拽著我的朋友跑,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我的這個機靈的小伙伴卻做了一件我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事,他突然一個箭步跨到我前面,把我向后一推,勇敢地用身體擋住了我,我還沒有明白怎么回事,美術老師的耳光就準確無誤地抽在我臉上。我人生的第一次友誼就這樣糊里糊涂被朋友出賣了。
這個故事讓D大笑不已,她幸災樂禍般地笑我笨,不過,她說,我父親不也是這樣,現在排擠他的,正是他親手帶出來的徒弟。說到這些,D又不快起來,D就是這樣,悲喜很快就形于色,為了讓她想點別的,我又為她講了一個與河有關的故事。
我跟你說過吧,我們離嶗山不太遠的,有一個時期,父親在嶗山里面采石頭。嶗山里有很多河,河水清甜干凈,父親說,喝起來味道象米湯。他們自己帶午飯,午飯就是那種結結實實的死面火燒,父親跟我講,他們的午飯是這樣吃的,在小河里用石頭圍一個圈,把火燒掰開,丟進去泡著,他們用樹枝做筷子,剛采出來的青石板做餐桌,一整條河就是他們的碗,有時候,他們還要沿著河奔跑,去追趕他們的午餐,因為水流得實在太急了。如果里面恰好還有魚的話就更美了,D笑著說。
你知道,水至清則無魚啊。我說。父親好結交朋友,和采石隊的一個年輕人最要好,那個人叫元紅,常來我家,我小時侯從沒見過象他那么漂亮的男人,身材修長,臉色紅潤,人也安安靜靜,來我們家做客的時候,常常一個人坐在椅子上望著窗外出神,一邊用牙齒仔細地咬自己的指甲,我母親也喜歡他,其實很多女人幾乎都在巴結他,他在的時候,我們家常常多出許多來找母親玩的年輕女子,唧唧喳喳地說笑,他卻總是不怎么吭聲,偶爾說起話也是一副害羞的模樣。然而誰也想象不到,這樣一個讓很多女人都醉心的年輕人,卻是個小偷,他偷東西已經到了入魔的程度,我就親眼見他不假思索地把父親的手表塞到自己的口袋里,然后嘆口氣,又拿出來放回原處。父親說,在采石隊,他們每天都能吃到他在附近的村莊偷到的瓜果,父親勸他收手,他總是靦腆而平靜地說,沒事兒。
有一天深夜,父親起來小解,那已經是初冬了,夜空清冷,山里一片靜謐,父親在返回帳篷的時候,突然聽到河的上游有人在痛苦地呻吟,他吃了一驚,壯了壯膽,朝那個方向走過去。在河邊,看到一棵大樹橫在地上,下面壓著一個人,是元紅,已經奄奄一息了。父親驚了一身冷汗,急忙跑過去,想把樹移開,這時,元紅在樹下喊了父親一聲,父親湊到他嘴邊,元紅說,哥,你先等等,如果這次我不行了,這件事,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就說是我自己摔的。元紅被連夜送到醫院,他的脊柱已經折斷,渾身都是血,父親覺得事情可疑,暗地里報了案,在元紅即將出院并得知自己下半身將終生癱瘓的時候,公安局的調查結果也出來了,調查結果是,元紅私自在山上偷伐山木,不幸被突然倒下的大樹砸中,導致重傷。也是在這個時候,采石隊的隊友才知道元紅還是個孤兒,在住院的半年時間里,沒有一個親屬前來探望。出院后的元紅生活成了一個大問題,采石隊看他可憐,便把他接回去,看管炸藥,父親說,從那以后,元紅幾乎不再和任何人講話,每天在炸藥倉庫前面的小河邊看著流水出神。采石場不遠有一座道觀,元紅偶爾也用兩只板凳撐著身子,挪到那里看人上香,這件事大家也就漸漸淡忘了。
又過了幾年,采石隊要撤出嶗山,元紅的問題又讓大家頭疼起來,父親說,我去求求那幫道士吧,他也許可以幫他們看個香火什么的,道士觀的好心道士因為一直可憐元紅,就同意收留他,并為他修補了一下那個曾經存放炸藥的小庫房讓他住,元紅每日幫道士們照看香火,道士們從香火錢里拿一點出來幫他打理生活,我在此后很多年都沒再聽到他的更多消息,父親每次提起這件事,總感慨萬千,這里面還有個插曲,采石隊撤退前,清點炸藥時,發現居然少了一百斤,因為元紅已經那樣了,大家也不好責怪他,采石隊的隊員因此被上級調查了一個月,父親還幫每個隊員寫了一份檢查,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很多年以后,我有一次陪父親去嶗山,路過當年的采石場,我們想起了元紅,順路去看他,他的身體已經好多了,可以用小板凳撐著連續走五里山路,最讓我們驚訝的是,他居然有了個女人,一同住在原來的小屋,屋里的擺設雖然簡單,卻干凈整齊。我和元紅開玩笑,說是不是該喊嬸嬸,元紅漲紅了臉,說還不是。那次,父親和元紅談了半夜,越談越激動,他們甚至要大吵起來,有幾次,我看到父親幾乎要從桌子邊跳起來,但第二天,無論我怎么問,父親卻對頭晚的談話內容只字不提,其實那時我還只是個孩子,這種事并不是我所感興趣的。直到五年以后,父親才在一次酒后,對我們說了元紅那次出事的真相。
那天晚上,元紅照例來到附近的村莊,這次,他想偷一只鵝和隊友們解解饞。父親說,一個屢屢得手的慣偷,一旦出事就是致命的,元紅那次剛翻過院墻,那戶人家養的一條狼狗就嗚的一聲咬住了他,而此前他在墻上往里面扔石頭試探的時候,那條狗正一聲不吭地躲在暗處,更可怕的事,這戶人家里剛好有五個齊刷刷的光棍兒子。那一夜,元紅一直被折磨到斷了氣,然后,他隱隱約約記得自己被人裝進麻袋,抬著走了很久,他聽到一個人說,綁塊石頭扔水庫里吧,另一個說,不如這樣,然后,就沒有了知覺。他再一次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躺在一棵伐倒的大樹底下,渾身卻是不能動彈了。
那我們得趕緊報案!聽到這里,我脫口而出。父親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次我和你元紅叔爭吵,就是為了這事,他該死不讓我報案,我問為什么,他提到了你那個未來的嬸嬸,你能相信嗎,那個女人是把他打殘的那五兄弟的親妹妹。父親嘆了口氣,那是個奇女子啊,兄弟做了孽,她自己心里不忍,便和家里決裂,獨自一人來到你元紅叔那里,要照顧他一輩子,那天,我看得出來,她對你元紅叔是真有感情啊。你元紅叔不讓報案,就是為了這個,說不想傷害這個女人,而且他對我說,他已經把這件事徹底忘記了。果真這樣,也何嘗不是件好事。
一九八六年,我們收到一封來自嶗山的信,是元紅叔的,信里說,他準備結婚了,和那個女人。但信中并沒有說明具體日期,也沒有邀請父親參加婚禮,信末有一句話,說,事情早晚總得有個了結。父親為此事感到不安,通過多方了解,得知,原來打殘元紅的那戶人家的老人,自覺將不久于人世,決定在死前了卻同元紅叔的這段恩怨,自己做主,把那個一直在照顧元紅叔的女兒許配給了他,并決定帶上五個兒子一同前去參加婚禮,從此,盡釋前嫌,抿卻恩仇。聽到這些消息,父親終于松了一口氣,作為元紅的好朋友,他知道,這件事情所能得到的最好結果,不過如此了,他還責怪元紅,說至少該讓他去參加婚禮,母親說,你以為這是好事啊,這種事,人家不好聲張的,父親覺得也是。兩個月以后,嶗山發生了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一樁爆炸案
案,爆炸發生在一個冷冷清清的鄉村婚禮上,大約一百斤炸藥頃刻間引爆,劈掉了半個山頭,塌陷的山石截斷了前面的一條小河并因此形成一個小水庫,死者中包含我的叔叔元紅和照顧了他近十年的我未來的嬸嬸,以及五個前來參加婚禮的中年男子和一個彌留之際的老人。
| 

 團隊博客
團隊博客 銳寫作
銳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