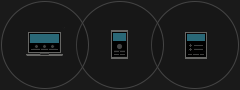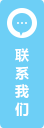|
南方之九 . 居住地
作者: its
|
发布: 2008/1/11 (14:47)
|
阅读: 78411
|
评论: 0
|
静态地址
|
内容源码
此行的目的,我对母亲说,是回去看看儿时的居住地。居住地?母亲望着我,脸上带着疑问。其实,就是出去转转,我赶紧说。母亲笑了,说,五十年前,你祖父说出去转转,结果就在那里留下了,三十年前,你父亲也出去转转,后来我们全家人都跟着去了,你们都是些怪人,我一辈子都不想那个地方,我什么地方都不想,除了自己的家。妈,我问,我想知道,当时我们走的那天,是不是十五,我老记着那晚是满月,五叔推着我,我们沿西岭大道去火车站,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满脑子的月亮在眼前晃。母亲回答说,是初六吧,五月初六,端午节的第二天。
很多年来,每次旅行,动身的前一天,我总忍不住和母亲谈一会儿,成年的男人用这种方式迷恋母亲,是件足令人羞愧的事,但旅行常勾起我心中离别的苦愁,觉得只有她才最理解这些,这大概就是少年时代的游历生涯在内心留下的痕迹。晚上从她那里回来,照例睡不着,便盼着早点上火车,想着一个人在路上的快乐,很多时候,快乐就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把自己忘掉,或者在遥远的异乡,随便想念点什么,而且我是这样喜爱火车,沉重的玻璃窗被两个人抬起来,干热的风灌满耳朵,远山,弯曲的河,还有没完没了的大平原,在这种时候,我甚至喜爱一些乏味的风景,透着那么一种寂寞味道,火车把旅行无限拉长,长到你不觉生出厌倦,最好的旅行就是含着厌倦,否则你永远都不会想念那些走过的路,还有,那些穿过秋野的摇摆夜晚,是我多年来最可靠的梦境。
母亲说是五月初六,那么,当时还是B的夏天,我们到达住地已经是深夜,那是一次奇异的旅行,傍晚出发,在深夜到达,我在火车上一共三天三夜的记忆,如今全然丢失了,那种感觉就象五叔直接用手推车把我们推到了目的地。那时,我从车上跳下来,周围是令人心悸的黑暗,象深不可测又充满阴险的水井,我需要仰起头,看着漫天的星星才站得稳。星星也让我内心感到塌实,五岁的时候,我已经熟悉了北半球星空大体的模样,那是夏夜在打麦场睡觉的收获,我还得过梦游症,睡到半夜,一个人走开,沿着打麦场的小路往家走,家里的大人常常在凌晨发现我睡在另一个打麦场的麦草堆里,这不值得大惊小怪,那时我并不害怕,却把家人吓坏了,他们说我的魂拴不牢,便把我关在家里睡,我依旧梦游,突然醒来后,看着黑漆漆的屋顶,惊恐得把衣服都尿透了。家人总想让我明白家里才安全,但在我看来,那个摆着水泥大瓮,有三个地窖,四个房间,塞满破烂柜子和祖传的器具的屋子才真正可怕,在打麦场,天上热热闹闹,足足有一千万颗星星在说笑,它们的事情我早就熟悉了,如果大人也知道天上的星星每晚都吵吵嚷嚷些什么的话,他们准忍不住笑出声来。来到B的第一个晚上,我用极快的速度扫了一眼星空,心一下子安静下来,当母亲说她已经完全掉了向的时候,我用手指着北斗七星说,那是北。现在,火车就朝着北斗星的方向开,山西已经过去了,我睡不着,莫名其妙地激动着,风从窗的缝隙灌进来,那是一种怎样的凉!让人忽然浑身充满力气,觉得身体是可爱的,它如此舒畅,象一种气味,迅速融化在空气与夜色里,记忆在一瞬间打开,我从没想到,自己的内心突然会涌起这么甜美的东西,在冰凉的青草的气味里,象种子逢着了雨水,如果没有雨水,种子的记忆就化作了泥土,我的记忆,有一天将化作清烟,但这一点也不令我伤感,我想,此行是值得的,不管为了什么,至少,我的身体,它一直被莫名的疲倦与郁闷所累,从冰啤酒与睡眠中寻找出路,我也厌倦了它,觉得它阻碍了我的快乐,但我在这样一个凌晨,坐在火车的玻璃窗旁边进入内蒙古,最先在快乐中苏醒的的,是我的身体。
祖父的小牧场的北面,有一条河,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乌加河。乌加河水泛滥的时候,形成一片浩淼的沼泽地,夏天被芦苇覆盖,冬天芦苇倒伏,露出零星的冰原。B只有夏天和冬天两个季节,而且夏天总是匆匆地就过去了,太阳最毒的日子,芦苇绿得发黑,让人觉得它们在狠狠地长,然而只消一夜北风,它们就悄无声息地枯败了,枯掉的芦苇地,从远出看,有四五岁的孩子所想象的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大群的水鸟飞进去,我经常在窗口的寒风中瑟瑟地趴着,看它们从北方的天空飞下来,成片成片地落在里面。祖父说,一整个冬天,它们就在里面过冬。我趴在北窗上,眺望芦苇地,心里满怀着渴望,希望有一天走进去,看看那个鸟的国家,在我的想象中,它们这样睡觉,每一群都围成一个圆圈,一个枕着另一个脖子,就象一群羊那样,互相取暖,这个想象把我迷住了,羊这样晒太阳的时候,我便挤到它们中间,从它们身上取暖,B的冬天直通通地冷,不过,没来B之前,到了冬天,我身上也这么冷。我趴在北窗时间久了,祖父就走过来,问,你老这么看,看什么呢?我没有办法告诉他,我在祖父面前异常地害羞,虽然认识他已经几个月了,每次看到他,心里总是惊慌失措。祖父说,从窗上下来吧,我们今天要把它糊起来,因为西伯利亚的寒流就要来了。我忍不住打了寒战,西伯利亚,这是个陌生而古怪的字眼,但一听到它,我的浑身立刻凉透了。西伯利亚寒流到来后的一个日子,祖父终于带我去了芦苇地,祖父说,只有冬天,沼泽地冻硬了,才可以进来,夏天这里根本没有路。祖父是去收集鸟的绒毛,他要用这些绒毛为我絮一双暖和的靴子,我穿上它以后,世界立刻变成暖融融的乐土,才知道自己每天都冷得发抖的原因是脚冷。在那片深不可测的沼泽地走了一天,我没有见到一只鸟,更没有象期待的那样,看它们挤在一起睡觉,我人生的幻灭感多半来自这样的儿时经历,这真令人难过。
在B,我现在没有一个熟人,即使他们小时候见过我,也断然不会把眼前这个行迹可疑的外乡人跟儿时的我联系起来,为了让自己的出现不至于那么突兀,我假称自己是地质队员,前来勘测乌加河的流量。然而地质队员接着就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我站在一条小水沟的旁边,向人们打听去乌加河B段的方向,他们用西北农民最善良的表情嘲笑了我一下,说,这就是。我吃了一惊,问道,很多年前,这里有一片芦苇地。他们又笑了,“外乡人”,他们说,“这里没有芦苇,这里草也没有,光有沙”。我开始怀疑自己行程的准确了,火车过了山西,进入内蒙,呼和浩特,包头,五原,路线是背熟了的,我坐在窗口,看了一路的大青山,从地图上,我找到了儿时所眺望的狼山在阴山的位置,从五原下火车,乘汽车到什巴,徒步穿过一块十里见方的沙化地,B就在眼前,然而眼前的B已经没有丝毫记忆中的模样,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装下去了,否则,我最好转身离开,沿着原路返回,然后,把这件事忘掉。所以,我便向那几个村民中年岁稍大说了这些话,
“你们也许不记得我了,大约三十年前,我住在这里,你们至少认得我的祖父,他住在芦苇地的南边,有一块小牧场,他的名字叫刘风锡,从口里来”
“那么,你们老家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一个老人说,“那些年间,有不少口里的人来逃难,说老家发大水,刘风锡我不认得,你们认得不?”他转身看着其他人,其他人都茫然地摇头,在那一霎那,我决定离开,心里也为自己的无趣感到恼怒,天快黑了,如果凑巧,还可以在天黑前赶上最后一班汽车,返回五原。我开始想念某个五原县城内的小旅馆,二层楼的小房子,房前是布满灰尘的树,四周这么静悄悄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叮当的饭盒,他们要去工厂上夜班,而我,坐在一片孤寂的异乡的夜色里,喝着啤酒,或者,随便看看天。
我第二次回去看B的时候,找到了不少还记得我的人,他们很惊讶我居然这么大了,在他们的眼里,我应该还是那个又瘦又弱的小孩,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在冬天,抄着袖子,在街上走来走去,不说话,也不笑。
“你还记得吧”,三爷爷说,他曾经是祖父最好的朋友,“有一年冬天,你差点死了。”
“真的?”我感到很惊讶。
“那年,我赶着马车去狼山拉煤,你死活要跟着去,你祖父就让去了。”
“半路上,起了暴风雪,我赶着马车,你坐在后面,冷得发抖,马跑得飞快,也不知道跑了多久,我感觉你似乎在后面睡着了,就转身看了一眼。”
“这一看把我吓坏了,你在车上没了。”
“我赶紧勒住马。这么大的雪,要是你睡着了从车上颠下去,不用多久,就没命了。”
“我赶紧顺着车辙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喊,一口气跑了五里路,我想这回完了,回去跟你祖父怎么交代。”
“我把每个雪窟窿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
“我没了主意,煤也不想拉了,就往回走,找我的车,回到车那里,才发现你躺在地上,脚上缠着根绳子,躺在雪地里,还真睡着了,我把你叫醒,你楞了大半天才明白过事来。”
“那么”,我问,“我们最终去狼山了没有?”
“去了,还拉了车煤回来。”
那一次回访,我登上了狼山,根据三爷爷的说法,我这是第二次来,但第一次的事,包括那次历险,都不记得了。狼山是阴山山脉众多山峰的一个,从祖父屋子的北窗,视线离开那片芦苇地,在北方云雾缭绕的地方,就是阴山,我认为那就是世界的尽头,我问祖父是不是这样,他说,也许是吧,但我立刻又不甘心起来,说,山的那边,至少也该有点东西吧,他说,还是山,于是,我绞尽了脑汁想出了这样的问题,有一天,我走到世界的尽头,前面已经没有路,无论怎么走,用脚,用船,用翅膀,都不能前进半步,那么挡住我的,到底是什么?
相关内容
| 

 团队博客
团队博客 锐写作
锐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