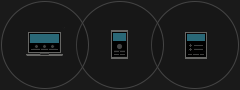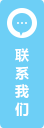|
南方之十三.山
作者: its
|
发布: 2008/7/24 (21:22)
|
阅读: 63243
|
评论: 1
|
静态地址
|
内容源码
山
D常说,她的家乡有很多山,到了X,我才明白很多山是什么意思,象稻田里生出的一片树林,一棵一棵拔地而起,塞满人的眼睛,不象北方,北方的山总要经过绵延的酝酿,从平原,到丘陵,起伏纵横,一座大山的方圆,常常有几百公里,这里的山更象园子里的盆景,有些精致,清秀,一种象竹子那样的清秀,象南方女子,细手细脚的,让初见的人惊讶。山原本是一些深邃的地方,在西北,山只有石头,一览无余,但站在山里,人始终被一种悲郁的气氛缠绕,仿佛静寂的背后是世界的尽头,在我的家乡,山平和了一些,那是些世俗的山,宽厚,善良,被乡人拿来作粮仓,柴房和石料场,从远处看,遮住了半面天空,走近了,只是个小土坡,母亲说,她平生最想做的,就是在山顶上找块石头,坐在那里看太阳落山,但小土坡的西面是一片比它还高的大岭,象一匹从天际斜垂下来的幕布,太阳几乎要沿着它滚落下来,我小的时候,以为大岭的末端有一个坑,太阳就落到那里面去,常想过去看看,想象看到太阳躺在坑里的模样,象一只巨大的柿子,我向它抛石头,或者用绳子把它拖上来,然而直到今天我也找不到大岭的尽头,那只是一片倾斜的土地,是大地给眼睛的错觉,冬天,西北风从大岭以外卷着沙尘长驱直入,那些蜿蜒的小路几乎象蛇皮一样被风吹走,广播站的电线,它们被架在涂了沥青的木头秆上,一个村庄连着一个村庄,电线的呜咽声令人胆寒,它发布的有关冬天的消息更令人战栗,而晴好的日子,耳朵贴在电线杆上,可以听到美妙的嗡嗡声,我对大哥讲,这就是电波的声音。
D说,我才二十多一点,就觉得自己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小时候,我一直住在这里,你看到了,周围全是山,父亲在楼下的车站上班,我站在这里喊,“爸爸--”,周围的山都回应“爸爸--”,我就对姐姐说,有人在学我,有一次,我数了数,回声最多有十七次。现在,这里盖满了楼房,再也没有回声了。你现在还敢喊吗?,我笑着问。不喊了,D说,但很想,很多次,我站在这里看着他,一套粘满油污的工作服,维修的车来了,他立刻仰卧着钻到地槽下面,我的心就紧张起来,担心他再也不会钻出来,有一次,我梦见一个人拿着软皮胶管往地槽里面灌水,我哭着跑下楼,往地槽里面望,里面再也没有了我的父亲。小时候,我常常这样哭着惊醒,父亲听到我哭,扔下手里的活,上楼来抱我看那些风景,这里的风景,看也看不完。我随着D的目光向远处看,这是个破烂的小县城,位于山与田野的边缘,一条河绕过半边城,水是嫩嫩的绿,我猜想那里面长满了鱼草,南方雨水丰盈,河与周围的土地连成一片沼泽,沼泽地里开满粉蓝色的蒲公英,也有白色的萝卜花。
什么时候,我们去那里转转吧,我对 D 说。去不了的,那里根本没有路,D 说,小时候,我沿着河走,希望找到河的尽头,我一直怀疑河水来自一个山洞,因为一年四季,河水都是冰凉的,有一天,我自己沿河走了五里路,河边的红土又粘又滑,我心疼脚上的塑料凉鞋,就脱下来挂在脖子上,父亲说,我小时候有些孤僻,只爱一个人玩,其实我只是想发现个巨大的秘密,讨他欢心。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不开心,但从没责骂过我们,他愁闷的时候,就站在阳台上,看着那些山,有时候一站就是两个钟头。那天家里人找了我一整天,然后去派出所报了案,公安局的人在沼泽地找到我的时候,我还在那里艰难地跋涉。T,你别笑我,不知为什么,在回家前的那些日子,我老梦见这些事,有一天我梦见河的源头是一个巨大的溶洞,我们打着火把进去了,在里面走啊走,我跟你说,坏了,怕是迷路了,你说不怕,我们就那样走了半天,出去一看,山那边居然是Z ,一想起这个梦,我就笑得要命,不过,如果这是真的,该多好。如果这样,我就可以每个月都回来看我的父亲了。你知道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他就要失业了,我对他说,我可以养活你和妈妈,他对我惨淡地笑了一下,我父亲今年刚好六十岁,五年前,他就应该退休的了。
我不曾知道,D的内心有这样一些情感,她多数时间象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对年长于她的,存着依赖心,她回到我身边以后,忽然连做饭,也不会了,如果我不去,她便吃快餐面度日。我做得一手好菜,喜欢看她吃得满头是汗,但有时候,爱情又不免让我空中楼阁起来,回家前,我曾想劝她和我一起去云南旅行,我对她说,我困在M快五年了,如果再不出一趟远门,怕要活活闷死,她不愿意,说云南有的,她们家也有,比如山。于是在D的家乡,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密集而奇怪的山,就象多年前的一个梦境,一座园子,里面有很多山,每一座都象一棵树那么大,我在梦中把它们伐倒,亘古绵延的秘密变成化石,虽然你永远也摸不透一座山,即使它在你脚下,然而当山倒下,躺在你身边,你觉得世界改变了,有一种伟大正在被你掌握的感觉,幸福象雨滴那样收藏到瓶子里,凤凰鸟落满手臂,流星堆在屋檐下,月亮上垂下软梯,而把太阳从碎石坑拖上来的感觉突然变得那样平淡无奇。
那天,为了重温一下D小时候的经历,找到那条河的源头,我和D在那些山间走了一个下午,最后,终于连河到底是往哪个方向流都糊涂起来,在现实中,这种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是很难的,河有无数的支流,每一条支流都可能把你引向困境,很难想象D在童年时代,有这样的耐心,当年她身陷沼泽地的地方在直线上离她家只有五百米,但茂密的蒲公英和芦苇肯定遮住了她的视线,如今,这里的蒲公英依然茂盛,如果不仔细看,你不会明白蒲公英是这样美丽的花,它们在风中摇摆的样子显得稚气十足,散发的药香带着苦清的味道,我想,春天,即使在湿润的南方也是显而易见的事,而我记忆中的春天是干燥而坚硬的,它只是一些细微的气味,被多梦而惶惑的睡眠放大,等着满耳的风声停息,等着一些事情发生,然而除了零星的回忆,你什么也等不到,夏天轰隆一声就来了。
我对D说,我们家的东边大约十里,有一片海叫丁字湾,从西岭大道上,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水,那里有座山,叫五龙山,我常想,站在五龙山顶看丁字湾,该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便一直想去看看。终于有一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去了,那段路并不远,却走了一整个下午,因为那些绵延纵横的乡间小路就和这条河的支流一样多。到了五龙山,天色就晚了,山上响着松涛,山那边的丁字湾或许正是铺天盖地的一片大水,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敢上山了,在那里犹豫了半天,只好掉转车头就往回赶,心里十分害怕,等到了家,又开始后悔,其实我后来知道,从五龙山上根本看不到丁字湾,走近了,丁字湾只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滩涂,人们在滩涂里建虾池,我儿时的一个伙伴,我叫他春左,后来就在那些虾池做工时淹死了。虾池很深吗?D问。我说,其实只有他的腰那么深,他划着船在里面喂虾,不知怎么就掉下去淹死了。你知道吗?他是个很机灵的人,小小的个头,比我矮一头,喜欢跟我玩,夏天,我去他家的瓜地帮他看瓜,瓜熟了,从瓜蒂上脱落下来,我就跟他说,咱吃吧,都掉了,他赶紧说,晚上它们还要长上去的。那个时候的小孩子把友谊看得那么重,如果有人欺负他,我可以豁出命和人家打架的。可是,有一次,他做了一件让我惊讶了很多天的事,我们便从此决裂了。我们的学校里,有一个美术老师,模样凶狠,又剃了个光头,我们都怕他,有一次,他从我们身边走过,春左忍不住骂了一句,小和尚,声音虽然不大,这个每日里都闷闷不乐的年轻人却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他象突然想起了什么要紧事那样咯噔一下站住了,拿手摩挲着自己的脑袋想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一声不吭地向我们走来。春左和我都吓呆了,那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拽着我的朋友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机灵的小伙伴却做了一件我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事,他突然一个箭步跨到我前面,把我向后一推,勇敢地用身体挡住了我,我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美术老师的耳光就准确无误地抽在我脸上。我人生的第一次友谊就这样糊里糊涂被朋友出卖了。
这个故事让D大笑不已,她幸灾乐祸般地笑我笨,不过,她说,我父亲不也是这样,现在排挤他的,正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徒弟。说到这些,D又不快起来,D就是这样,悲喜很快就形于色,为了让她想点别的,我又为她讲了一个与河有关的故事。
我跟你说过吧,我们离崂山不太远的,有一个时期,父亲在崂山里面采石头。崂山里有很多河,河水清甜干净,父亲说,喝起来味道象米汤。他们自己带午饭,午饭就是那种结结实实的死面火烧,父亲跟我讲,他们的午饭是这样吃的,在小河里用石头围一个圈,把火烧掰开,丢进去泡着,他们用树枝做筷子,刚采出来的青石板做餐桌,一整条河就是他们的碗,有时候,他们还要沿着河奔跑,去追赶他们的午餐,因为水流得实在太急了。如果里面恰好还有鱼的话就更美了,D笑着说。
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啊。我说。父亲好结交朋友,和采石队的一个年轻人最要好,那个人叫元红,常来我家,我小时侯从没见过象他那么漂亮的男人,身材修长,脸色红润,人也安安静静,来我们家做客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出神,一边用牙齿仔细地咬自己的指甲,我母亲也喜欢他,其实很多女人几乎都在巴结他,他在的时候,我们家常常多出许多来找母亲玩的年轻女子,唧唧喳喳地说笑,他却总是不怎么吭声,偶尔说起话也是一副害羞的模样。然而谁也想象不到,这样一个让很多女人都醉心的年轻人,却是个小偷,他偷东西已经到了入魔的程度,我就亲眼见他不假思索地把父亲的手表塞到自己的口袋里,然后叹口气,又拿出来放回原处。父亲说,在采石队,他们每天都能吃到他在附近的村庄偷到的瓜果,父亲劝他收手,他总是腼腆而平静地说,没事儿。
有一天深夜,父亲起来小解,那已经是初冬了,夜空清冷,山里一片静谧,父亲在返回帐篷的时候,突然听到河的上游有人在痛苦地呻吟,他吃了一惊,壮了壮胆,朝那个方向走过去。在河边,看到一棵大树横在地上,下面压着一个人,是元红,已经奄奄一息了。父亲惊了一身冷汗,急忙跑过去,想把树移开,这时,元红在树下喊了父亲一声,父亲凑到他嘴边,元红说,哥,你先等等,如果这次我不行了,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就说是我自己摔的。元红被连夜送到医院,他的脊柱已经折断,浑身都是血,父亲觉得事情可疑,暗地里报了案,在元红即将出院并得知自己下半身将终生瘫痪的时候,公安局的调查结果也出来了,调查结果是,元红私自在山上偷伐山木,不幸被突然倒下的大树砸中,导致重伤。也是在这个时候,采石队的队友才知道元红还是个孤儿,在住院的半年时间里,没有一个亲属前来探望。出院后的元红生活成了一个大问题,采石队看他可怜,便把他接回去,看管炸药,父亲说,从那以后,元红几乎不再和任何人讲话,每天在炸药仓库前面的小河边看着流水出神。采石场不远有一座道观,元红偶尔也用两只板凳撑着身子,挪到那里看人上香,这件事大家也就渐渐淡忘了。
又过了几年,采石队要撤出崂山,元红的问题又让大家头疼起来,父亲说,我去求求那帮道士吧,他也许可以帮他们看个香火什么的,道士观的好心道士因为一直可怜元红,就同意收留他,并为他修补了一下那个曾经存放炸药的小库房让他住,元红每日帮道士们照看香火,道士们从香火钱里拿一点出来帮他打理生活,我在此后很多年都没再听到他的更多消息,父亲每次提起这件事,总感慨万千,这里面还有个插曲,采石队撤退前,清点炸药时,发现居然少了一百斤,因为元红已经那样了,大家也不好责怪他,采石队的队员因此被上级调查了一个月,父亲还帮每个队员写了一份检查,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很多年以后,我有一次陪父亲去崂山,路过当年的采石场,我们想起了元红,顺路去看他,他的身体已经好多了,可以用小板凳撑着连续走五里山路,最让我们惊讶的是,他居然有了个女人,一同住在原来的小屋,屋里的摆设虽然简单,却干净整齐。我和元红开玩笑,说是不是该喊婶婶,元红涨红了脸,说还不是。那次,父亲和元红谈了半夜,越谈越激动,他们甚至要大吵起来,有几次,我看到父亲几乎要从桌子边跳起来,但第二天,无论我怎么问,父亲却对头晚的谈话内容只字不提,其实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这种事并不是我所感兴趣的。直到五年以后,父亲才在一次酒后,对我们说了元红那次出事的真相。
那天晚上,元红照例来到附近的村庄,这次,他想偷一只鹅和队友们解解馋。父亲说,一个屡屡得手的惯偷,一旦出事就是致命的,元红那次刚翻过院墙,那户人家养的一条狼狗就呜的一声咬住了他,而此前他在墙上往里面扔石头试探的时候,那条狗正一声不吭地躲在暗处,更可怕的事,这户人家里刚好有五个齐刷刷的光棍儿子。那一夜,元红一直被折磨到断了气,然后,他隐隐约约记得自己被人装进麻袋,抬着走了很久,他听到一个人说,绑块石头扔水库里吧,另一个说,不如这样,然后,就没有了知觉。他再一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棵伐倒的大树底下,浑身却是不能动弹了。
那我们得赶紧报案!听到这里,我脱口而出。父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次我和你元红叔争吵,就是为了这事,他该死不让我报案,我问为什么,他提到了你那个未来的婶婶,你能相信吗,那个女人是把他打残的那五兄弟的亲妹妹。父亲叹了口气,那是个奇女子啊,兄弟做了孽,她自己心里不忍,便和家里决裂,独自一人来到你元红叔那里,要照顾他一辈子,那天,我看得出来,她对你元红叔是真有感情啊。你元红叔不让报案,就是为了这个,说不想伤害这个女人,而且他对我说,他已经把这件事彻底忘记了。果真这样,也何尝不是件好事。
一九八六年,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崂山的信,是元红叔的,信里说,他准备结婚了,和那个女人。但信中并没有说明具体日期,也没有邀请父亲参加婚礼,信末有一句话,说,事情早晚总得有个了结。父亲为此事感到不安,通过多方了解,得知,原来打残元红的那户人家的老人,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决定在死前了却同元红叔的这段恩怨,自己做主,把那个一直在照顾元红叔的女儿许配给了他,并决定带上五个儿子一同前去参加婚礼,从此,尽释前嫌,抿却恩仇。听到这些消息,父亲终于松了一口气,作为元红的好朋友,他知道,这件事情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不过如此了,他还责怪元红,说至少该让他去参加婚礼,母亲说,你以为这是好事啊,这种事,人家不好声张的,父亲觉得也是。两个月以后,崂山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桩爆炸案
案,爆炸发生在一个冷冷清清的乡村婚礼上,大约一百斤炸药顷刻间引爆,劈掉了半个山头,塌陷的山石截断了前面的一条小河并因此形成一个小水库,死者中包含我的叔叔元红和照顾了他近十年的我未来的婶婶,以及五个前来参加婚礼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弥留之际的老人。
| 

 团队博客
团队博客 锐写作
锐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