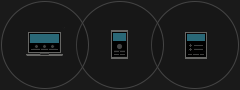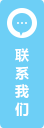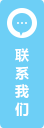如果地震台预告明天有地震,G大得都让人懒得逃走,黄曾经这样描述G。这是一个早晨,我刚刚从G城的好睡眠中醒过来,窗外是一片树林,地上满是土灰色的树叶,它们都是三四年前的落叶了,一直那么堆着。这很容易让人忘记现在的季节。树林中有一个不高的水泥屋子,没有窗,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那是个什么建筑,这时,鸟喳喳地叫起来,也许它们早就叫了,只是我刚刚意识到。这大概是最好的境地了,破旧又偏僻,这样的早晨,似乎被神遗忘了的一段好时光,有一种偷偷的喜悦。园子里没有一个人,我很想进去走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植物悄无声息,内心便有那么一种灰扑扑的快乐感,很多快乐,人匆匆就尝试完了,如果不是昙花一现,多半也让人事过之后心怀愧疚,惟独这样静悄悄的暗喜才会持久,就象一条狗,叼着食物走到角落里去,独自待上那么一会儿,有这么一会儿,也就心满意足了。我满心喜爱这里参天的古木,一整座园子,古红色的老房子掩映其间,我自小喜欢高大和宽厚的东西,比如马,树,大山和身边那些年长而老实的人。马宽容,树温暖,大山,恒久而神秘,我曾经多少次在傍晚远眺崂山,缭绕山间的云象火一样红,太阳悠忽而谢的时刻也有无尽悲风侵透少年人的心。西墙外也曾有过一片树林,生的是梧桐和臭椿,蝉脱壳的季节,每天可以在树下拣到一口袋蝉蜕,卖到中药站,一分钱一只,春天在林子里牧鹅,有一回,我追赶一只鹅的时候把它踩死了,这相当于创下一个大祸,天黑了,我坐在死鹅旁不敢回家,一个人,长着一张马脸,又丑又高,他正在旁边浇白菜,便走过来,捡起那只死鹅,说,还是只母的,然后,放回原处,叹着气走了。他实际是个傻子,至少村里人这么认为,我们叫他长云。他母亲因为得了严重的角膜炎,眼睛周围总是粘着眼屎,人们叫她日本娘们儿。他有一个哥哥,家里人费尽周折为他娶了媳妇,其实是拿她妹妹换的。结婚那天,很多人去闹洞房,因为他们家这样卑微,所有的闹房人到头来都极不尊重起来,事态几乎失去控制,新娘已经开始掉泪,这时,长云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根绳子,挽了个扣,套住为首的一个人的脖子,一声不吭地把他勒了足足有一分钟,那个人最终侥幸捡了条命,从此远远地见到长云便浑身发抖。长云放下我的死鹅走开后,我连一秒钟都没敢耽搁就跑着回家了。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是因为这里的古木让我想起西墙外的那片梧桐与臭椿杂生的树林,内心象一盏灯那样亲切起来。长云在第二年的夏天死在南沟的水塘,一个收废品的外地人在那里洗瓶子,不知怎的便落水了,长云听到呼救,第一个赶到那里,一个猛子扎下去,头扎在陈年的淤泥中,脚还露在水面上。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梦的境地,把过去的梦整理一下,发现那是个完整的四维世界,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你不必考虑时间,我常常梦见十年前梦见的一个地方,也会把当时中断的情节继续下去,比如曾有一座入云的山,上山的路,却是幼年时常走的一条乡路,我一边走一边想,山那边就是北冰洋,最后的情节就不记得了。左晚莫名其妙地梦见了北冰洋,水是冰冰的蓝,我忽然想起了那座山,果然还在,便从山顶下来,走到一个地方,我对自己说,当时那个梦,就是从这里断的。我还梦见过一个地方,也是冰冰蓝的水面,但当时并没觉得是北冰洋,现在想来,那两个画面是一模一样的。在那个梦里,我在结了冰的水面行走,冰一直嘎嘎地响,我便安慰自己说,别怕,人是永远都不会梦见自己死去的。
上次来G是陪着D,天一直阴沉着,我们慢腾腾地走,G这个庞然大物,每天有一千万人在里面分赃,如果你带着异乡人的面孔,上街,加入到队伍,把这个叫做生活,或者娱乐,你就有被分掉的危险,所以,在G,我从没真正欢乐过,一千万人在街上毫无头绪地争夺时间,你就象在台风眼支起一把躺椅,我不只一次地沿着地图穿过G,这是步行者最难征服的一个地方,你要同汽车,小偷,二痒化碳和更多快腿的人赛跑,所以,尽管我早已习惯用散步消磨时光,在G,我们只好钻进汽车,从一个站逃向另外一个站,听满街的人嗡嗡地响,看计价器象点钞机那样跳动,我们频繁地查看时间,从巴士的站牌上读站名,我们就这样在两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一起谈爱情。D说,从火车东站到西郎,全程六元,我们只买了两元的单程票。于是,D惊慌起来,这是个极度爱面子的城市,但我们忽然爱上了这个地方的地铁系统,它躲在地下,有凉爽的风,除了铁轨的声音,剩下的就是寂静,当我们钻入地道,象一对鼹鼠,忘记时间,太阳,和复杂的生活,我们相互偎依,取暖,谈话,看着对方的眼睛,我们终于看到了G的爱情,全长三十六公里,摄氏二十度,很多年以后,还会怀念那一天,在地下五十米,拥抱着D。当我们返回地面,我们已经累计欠下地铁公司二十元的票款,但没有人知道这些,我们用一个小时,加上爱情,Hack了G城地铁的收费系统。
“你已经一动不动地站在这里一个小时了。”黄对我说。
“我在看这个园子”,我说,“又想起了老家的那个林子和许多乱糟糟的往事。”
“今天,你好好出去转一转吧,这个季节,G说起来,还是挺热闹的一个地方。”黄这样建议我说。
我却一瞬间灰懒起来,觉得G不过如此,慕着名去看一个地方是件无趣的事,而且人的一生,总有无数际遇是无意中得到的,比如九六年在拉萨,一路颠簸了几千公里,我却很快把那些伟大的风景淡忘了,大昭寺,八角街,布达拉宫还有滚滚的拉萨河,最想念的,却是西藏日报社的招待所,那个小小的院落,肥手肥脚的女管理员,接自来水的石头台子,房檐下一溜花花绿绿的脸盆。每天傍晚,我买来啤酒坐在那里喝,觉得悄悄寂寂的生活有一股容易承受的甜蜜,或者说,幸福,就是你恰好需要幸福的时候遇见的任何一件事。所以,我对黄说,“我实在懒得出去,如果不打搅您,就在这里待一会儿吧”。
“你这个奇怪的孩子,”黄说,“你乘了两个小时的车来到G,又步行三十公里找到这里,就是为了在这个草木缭乱的地方陪我发愣。”
“九六年在拉萨,”我说,“在西藏日报社的招待所,我遇见了一个同乡。他待在那里已经六年了,我们见面的第一天,他就约我喝酒,对我讲他的事,说他怎样厌恶回家,怎样搪塞自己的妻子,怎样和野女人私奔,怎样做虫草生意却没赚到一分钱,他一点也不悲伤,也不后悔,始终笑嘻嘻的,象讲别人的故事。然后他向我借钱,我一点也没犹豫就借给了他,谁知在回招待所的路上,他又莫名其妙地把钱还我了。”
"小时候,"我接着说,“冬天,我浑身冷得发抖。出太阳的日子,十字街的墙脚,一群老头儿,披着大棉袄,蹲在那里晒太阳,我羡慕得要命,想,赶紧快点变老吧,就可以和他们一起,眯者着眼,过那等好日子。人经常有一些奇怪的愿望,我母亲曾对我说,她最想的,是坐在山头上,吹着凉风,看太阳落下地平线山。每次想起这些,心里总有些发酸。你肯定奇怪我为什么说这些没头没脑的话,我也奇怪。你知道,我每天的生活,非常狭窄,几乎不需要我去选择,任何事情都象注定的一样,我常想,为什么M的生活这样单一,老人坐在窗口发呆,孩子顶着黄头发看漫画,其余的人,都待在一个他最痛恨的地方盼着下班。就连在充满胡思乱想的G,也是一样,我岂不知道这里有百年的骑楼,上好的烤鹅,缓慢流淌的珠江水和一北京路的漂亮女孩,但我总想等待一些愿望出其不意地从记忆中跳出来,然后看看眼前的生活,它是否是某个愿望的延续。”
我这样说着的时候,黄阿姨已经倒在她的躺椅中沉沉地睡着了。她后来在给我电话中,一边埋怨我的不辞而别,一边抱歉自己的失礼。接着,她对我说,“不过,那天,我真的睡了个很香甜的好觉,梦见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一开始,你说的那些话,我觉得有些烦,在G,没有人会花二十年去记住一个愿望,可我又想,有一些愿望,可能你并不是真想实现。另外,你的那个 D ,她现在是否有什么消息了?”我说,“有,但她的事,在电话里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 |